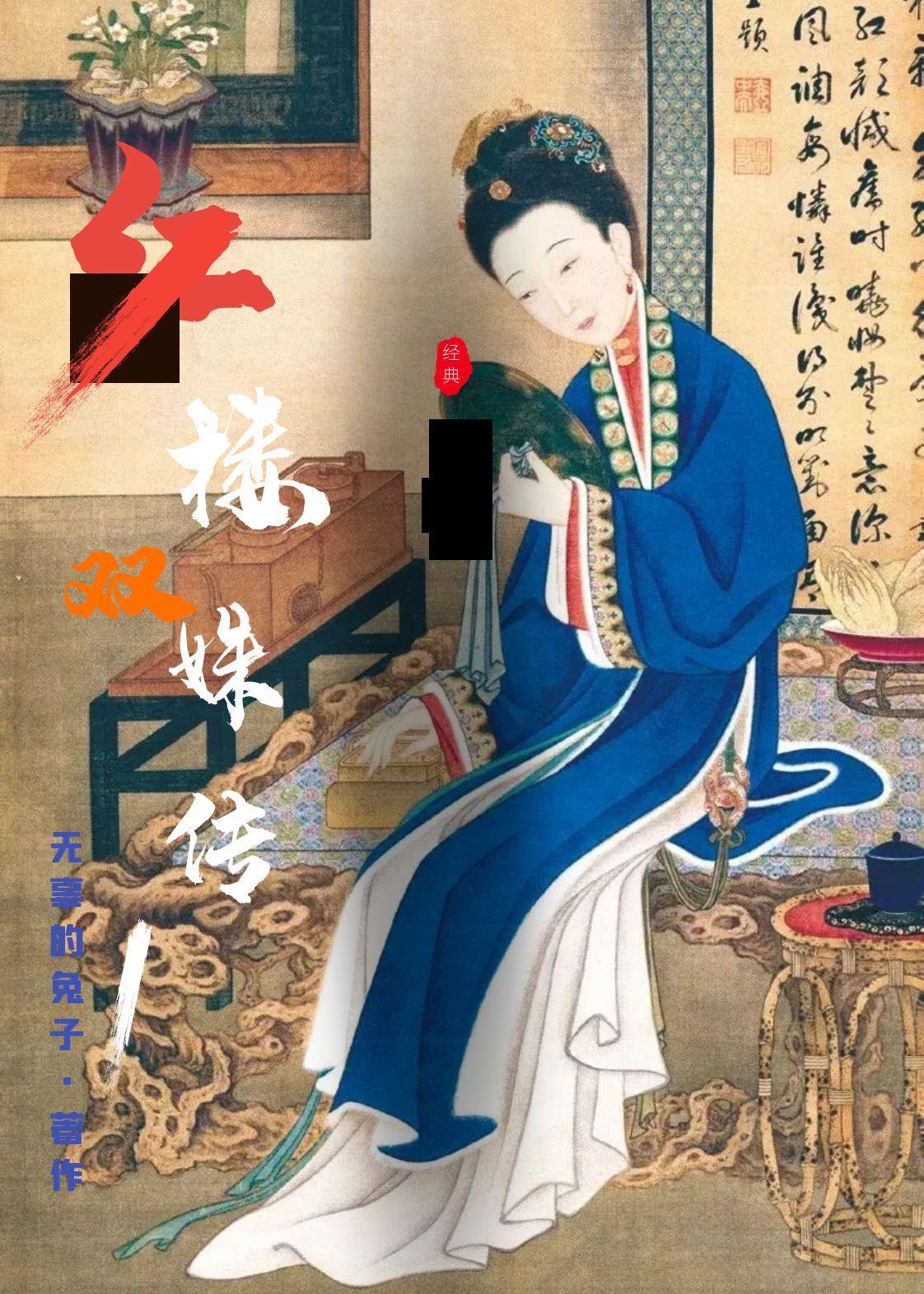极品中文>创造一个角色的关键点是什么 > 何谓剧本(第1页)
何谓剧本(第1页)
何谓剧本?
说起戏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之一是主题、情节,换言之,是“剧本”。
如果你对你的小狗吹声口哨,说一句“来吧,去散步!”,狗儿肯定闻言即起,围着你欢腾雀跃——此时此刻它是在就它的主题进行表演:出于本性、快乐或者感恩而喜不自胜。
每一部哑剧、每一出舞蹈,都必须拥有一个特定的主题。没有了主题,你的舞蹈无非是一连串把身体扭来扭去的动作而已。
主题、情节或曰剧本,是作者关于更好的生活,或者其中某一特定阶段的认知所被赋予的具体形式。
生活的核心,是以所有或简单或复杂的表现形式加以展示的灵魂或者人类精神。
值得一看的戏剧,关注内心生活必然甚于关注我们日常生活的外部事件。
演员们会说某些角色“很舒服”,另一些角色则“出力不讨好”,这意味着有些角色充满了精神内涵,演员的灵魂可以轻松地、热情地与之呼应,从而创造一个形象——一个鲜活的人物;而另一些角色只能从外部着手来建构,缺乏内在的精神逻辑。这样的角色流于空洞,演员会发现其中没有什么创作可言。
生活教会我们,每一种感情、每一个有所求的欲望——都必须被“表演”或“上演”。
如果我恳求你们为我做什么事,我必须“表演”我的祈请之意。如果我冲你们喊“救命”——我必须“
表演”威胁我的险情。
如果我试图劝服你接受某个观点,我必须“表演”自己头脑的优势,换言之,我必须让你看出我对在哪里。
这才是每个剧本的基石。
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教学中使用了“人—角色”(man-role)这一表述——就像皮兰德娄的六个角色#pageNote#0——我们不妨称之为“活生生的人物”。所以——戏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物”都必须拥有精神驱动力,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勇往直前,并给予演员机会,把这种驱动力以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表现出来。举例来说,如果剧作者写了一段长篇大论的独白来讲述人物致死的原因,你怎么能够令人信服地饰演一个垂死的人呢。
只有依托人类的真情实感来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剧作家才能够创作出真正的戏。他也许能构建形式,设想出表达情感的手段,但是他无法虚构出情感本身。
自然法则是不变的、永恒的。
但是神圣丰饶的大自然体现自己法则的方式却不拘一格。
自然法则教导我们,我们的整个生活无非是一连串的奋斗,一心要让生活更上一层楼。
狗儿们为一根骨头打得不可开交。逐利之争,人亦难免,特别是骨头上还连着一块肉的时候。
然而大多数人倾力以求的是自己的精神理想。
世上的生灵,从微生物开始,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奋斗中。奋斗停息,生命即告终止。
以
创作呈献给世人的剧作家必须遵循这一法则。没有哪出戏会缺少源自观念、激情、情感和欲望的奋斗。在生活中,这种奋斗表现为一系列关乎意志的问题,由我们的智识和精神来决定,并由我们的生理器官来执行。
我心存高远——我要拼尽全力,一酬壮志。我坠入爱河——我要想方设法,打动芳心。以此类推,连最琐细的问题也不例外。
我想洗洗脸——我要借助毛巾和肥皂来完成这件事。
换言之,我们的整个生活是由一系列问题构成的,而表述这些问题的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因素(或曰论点):
我想
我做
没有这两个因素,剧本就无从谈起了。除非我们能够把这两者应用于角色的任何方面,否则我们有的不是剧本,只是堆砌的辞藻。
如果你拿到一部真正的经典剧本,你会发现,这两个因素可以应用于其中的任何角色。的确,棘手的情况在所难免,例如“我想讲述,我想解释”——然而,一旦悉心参透这出戏的精神,你总能发现角色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动作。
在生活中我们通常会遭遇两类问题:
主要问题,在人生的特定阶段会占据一个人的整个身心——比如爱情、野心……
次要或辅助问题,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比如请求、说谎、爱抚、劝服……
说到一部戏,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有一个,或者
至多两个主要问题,覆盖整部戏,几乎是所有角色的主旋律;再有若干次要问题为辅,以引发主要问题。
举例来说,在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TwelfthNight)中,主要问题是:如何得意尽欢,如何及时行乐。这个问题纵贯全剧,串珠成线。次要问题则协助推动主线的发展。
戏剧的头等大事就是开掘主要问题——要打造一部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排练时间有一半会奉献给这个步骤,但是一旦主要问题定下来,整部戏就轮廓清晰,融会于同一个目标之下了,这是每一部艺术作品都不可或缺的最必要的前提。不幸的是,许多剧作家对戏剧的文学性孜孜以求,逐渐淡忘了戏剧要忠实于“生活问题”。
关于此类剧本,我可以举某些法国“浪漫主义”、所谓“伪古典主义”的,出自高乃依、拉辛甚至维克多·雨果之手的剧本为例,#pageNote#1这些剧本卖弄长篇大论的台词与华而不实的独白——言辞丰赡,却没有展示“更好的生活”,仅仅是呈现了一批浮夸、虚饰的人物,还被剧作家带入矫揉造作的伪悲剧或伪喜剧泥沼。
仅仅因为舞台如童话,诸事俱可为——有些剧作家就奉行他们的“书斋空想”,罔顾“生活的真相”,为演员和观众拿出的是向壁虚构的主要问题。他们的目标仅仅是展示新奇的、“机变百出”的情境——而
不是高于现实生活的点点滴滴。结果,演员的表演生硬刻意,“戏剧化”与“做作”成了同义词。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所有虚构的人物都像暴风雨本身或者花草树木一样平实自然,因为其间的人类情感反映出了大自然本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