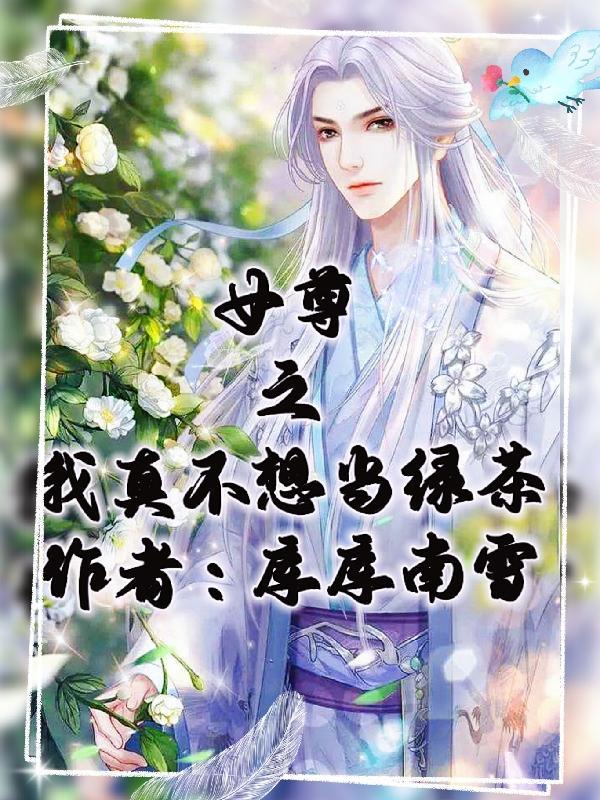极品中文>煞神方位在东方是什么意思 > 第29页(第1页)
第29页(第1页)
欢喜精明得很,定北候拿到户部册子的消息谁说谁倒霉,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还是让别人做的好。
“嗯。”达步陵昊点点头,“那边没事就好,沈开好几天没过来。你明日去国子监仔细问问,看看他缺不缺东西。”
“是。”欢喜行了礼,正要躬身退下。见达步陵昊目光呆滞,怔怔地望着窗外,不禁出言道,“王爷,您真想定北候就去看看她。这样熬着,小的们看了也难受啊。”
达步陵昊微微一笑:“我是想她,可她不想见我,见了面两人都只会更难受。”
窗外阴沉沉的,灰得看不出色彩,映着他的笑容,无比惨淡。
过了几天,忠王府送来了喜帖,忠王妃的义子秦小二成亲。秦小二深得忠王夫妇宠爱,达步陵昊自然要给忠王面子。
忠王府里的宴会没有妖娆的美女,满座的达官贵人们也不敢在忠王眼皮子底下放浪形骸。但在丝竹音乐声里,大厅里照样一派喜气洋洋,无比热闹。
沈圆月坐在最冷清的一角静静地喝着酒,她虽然不喜欢这种场合,但忠王是凌羽的义父,不来实在说不过去。没人敢嘲笑她的笨拙,更没人敢好奇地打量她。
时辰到,新人开始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本是无父无母的孤儿,得忠王妃照顾收为义子,如今高官得做,又娶了世家女子为妻,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拜完天地,又带着新娘一起结结实实给忠王夫妻磕了好几个响头。
将一对新人送入洞房,达步陵兰端着酒坐到沈圆月旁边,笑道:“当年我与将军共破临州城时,将军家的小开才出世不久。如今后辈到了成亲的年纪,咱们也老了。等小二成亲后,我欲向皇兄辞行回越裳封地。离开越裳时我家笠儿还未出世,现在已长那么大,皇兄对我应再无戒心,可以回去了。”
“嗯,王爷保重。”沈圆月垂下眼帘,若有所思,“只是从我枪下逃掉的那人现今在南方活动,王爷当心。”
别看忠王夫妻感情和睦,追溯到过去也有那么一些不光彩的历史。忠王妃本是临州城守之妻,让忠王连哄带骗弄到手。忠王妃对前夫有旧情忠王自然不安心,沈圆月因与忠王交好,攻下临州后,督着手下翻尸体守路口,将正易容逃跑的临州城守揪了出来。只是那人武艺不差,硬是从枪神的银枪下逃得了一条性命。
能在自己的枪下走上一百回合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沈圆月藏了私,一直暗暗关注着那人的行动。期盼和那人再战一回,解解手痒,顺便弥补她对战史上极不光彩的一笔。明明白白要击毙的敌人竟然逃了,心里真不舒坦。可惜啊,那之后忠王就改了主意,想留那人一命,不许她再追查。
达步陵兰看着眼前闹哄哄的宾客,不动声色:“将军虽没为我除掉他,却废了他一身武艺。初弦已为我生儿育女,那人早已不打紧,暂时留住他的性命,将来能为我所用也未尝不可。将军有何打算,想放弃陵昊?恕我直言,乾王对你动了真情。跟着他不失为一个好去处。当然,依将军现在的光景,根本无需倚靠男人。就算将军与其他人成亲,本王也祝将军百年好合。”
沈圆月便不说话了,嘴唇抿得紧紧的。
“你已征战多年,如今天下太平也放放戒心了。挑个好男人作伴,给小开找个爹爹,和和乐乐过日子多好。不管是男人女人都该有个安稳的窝。”那边有人来贺喜,达步陵兰忙过去应酬,临走时丢下也不忘丢下这几句话。
沈圆月依旧静静地喝着酒,只是神色越发恍惚。
忽而有人进来通报:“乾王殿下来了。”
声音不大,传入耳中却一个激灵,恍恍惚惚的意识逐渐清醒了过来。抬起头,对上了一双笑盈盈的桃花眼。那人正对着自己摇着扇子浅笑,腰间挂着一块中间夹杂着许多杂质的玉佩。
“这么久才来。”达步陵兰迎过去。
“恭喜。”达步陵昊说着话,眼睛却一直紧紧地盯着不远处暗红色的身影。病痛可以忍过去,可刻骨的相思之痛怎么忍得了?
被达步陵兰拉着在主位上坐下,立刻有人凑过去寒暄:“乾王殿下好久不见,咦,您腰间的玉佩玉质甚奇,是什么宝物?恕小的眼拙不认识,还望殿下解答一番。”
达步陵昊摇着扇子只是笑,一边用眼直直地盯着不远处的人。
有那懂事的知道其中渊源,忙让开了两人之间的空间。也有那傻子因对乾王带着块下等玉感到好奇,追问个不休:“这样特别的玉到底妙在哪里,殿下不说,小的真不明白。”
那边的沈圆月听到他们的对话,只淡淡地瞥了这边一眼边将头扭向了别的方向。达步陵昊顿了顿,拉过衣袖将玉佩遮住:“玉是几年前别人送的,不稀罕。”
“哈哈,玉不稀罕,稀罕的是送玉人的情意。”某个自作聪明的人大声笑了起来,“见殿下如此珍爱此玉,必是美人所赠。”
众人哄笑,纷纷猜测是哪位美人能得乾王挂心。会不会是借怀孕逼乾王成亲,后被乾王弄得身败名裂的美人?又或许是那雪姬?都是大美人,对某人痴心一片只换来几天温存,接着就被甩掉了,真浪费。
几乎没人将玉佩和不远处的煞神联想起来,这两人以前有情大家知道,两人分开的事大家也知道。只是在众人看来,煞神和男人没什么区别。今天她和乾王好,明天身边就领着个男宠。这样一个不是女人的女人,怎么会为情黯然神伤?所以没有人避讳她的存在。
和他们想的一样,这边在追问乾王的玉佩,那边的沈圆月依旧若无其事地喝着酒。
正在说笑,一个年长的吏部官员端着酒走到沈圆月面前,躬身道:“定北候不日将大喜,敢问婚期定在何时?到时老夫定登门祝贺。”
沈圆月怔了怔,拿酒杯的手僵在了半空。她看了主位上的达步陵昊一眼,半天,才用清晰的声音缓缓道:“十一月初五。”
四周喧哗成一片,连人的声音都微弱不可闻。达步陵昊一边喝酒一边和旁边的人说笑,似乎根本没听见他们的交谈。
两个曾经贴得很近的人,相隔不到百步,距离却超过了万水千山。
宴会继续进行,沈圆月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也不知喝了多少。待酒劲上头,她起身告辞想离开。刚走到门口,忽然听见身后一阵噼里啪啦作响。回头一看,只见达步陵昊晕倒在地上已没了知觉,身下是一堆酒壶碎片,刺眼的鲜血混在清冽的酒里无声地流淌。
心脏一阵紧缩,急忙跑过去:“王爷。”
太医说达步陵昊只是醉得太深,一时醒不过来,没什么大碍。只是胳膊被酒杯的碎片刺得太深,流血较多。既然无碍,替他清理干净伤口灌了醒酒汤,众人便退了出去。
见沈圆月盯着床上的人没动弹,达步陵兰道:“将军,乾王就托付给你了。”说完关上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