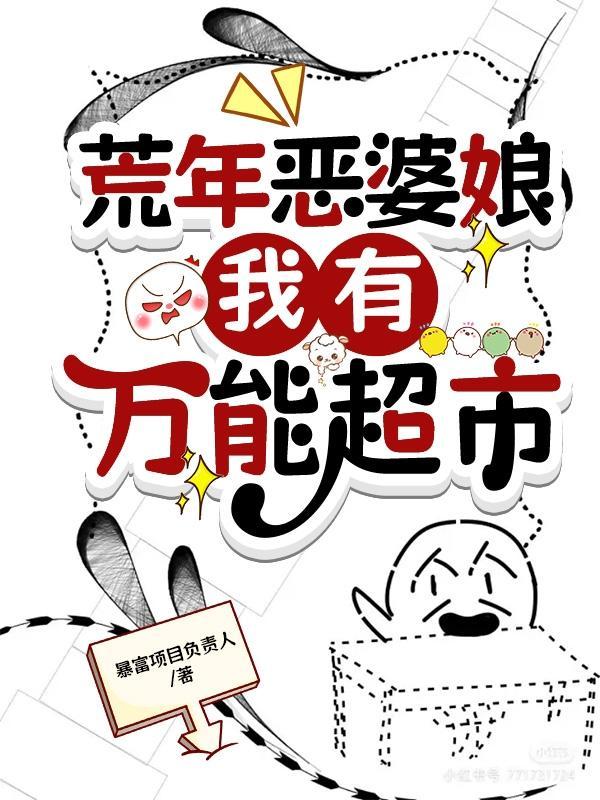极品中文>剖天在线阅读 > 第十章 风暴潮三(第2页)
第十章 风暴潮三(第2页)
这块表是品味的象征,能把他和戴金色劳力士的暴户区分开来,吸引到真正的气质女,就像林芳那样的。
“你都问我几百次了?我再告诉你一遍,有,明显有。这9点半的图上都显示有,我也拜托张台请示过上级了,这是今年在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第2个台风,内部编号95o2。”任天富说完叹出一口气,又刷新了一次窗口。
“那它到底来不来咱们这里?”张勇表情木讷,语气机械。
张勇是被分配来见习的,家人都住中山,正在五桂山上旅游。即便大学四年里去舞厅的次数比去教室的多得多,他也能知道,风暴潮这种东西,比海啸的能量小多了,一遇到大地形就熄火,跟他没关系,跟他家人更没关系。
他只想早点睡觉,平安熬过没剩几天的见习期,拿到毕业证,和林芳一起成为金贵的本科毕业生,跟这个穷地方说再见。
“我觉得不会。你看之前的云图上,副高东撤并且很弱,这种情况下,台风不容易往西走,之前也一直往北。而且咱们这里6上有稳定高压,就算想来也会把它给挤走。”任天父一板一眼地说。
“那你紧张什么?”张勇把视线移到任天富的右手上,那只青筋暴起的手不断点着鼠标左键,动作快到像要抽搐。
“昨晚9点半不来不代表今天1点不来。风云天气,瞬息万变。”任天富终于被耗尽耐心,松开鼠标把手重重捶在桌面上,“小日本的东西,真不靠谱!”
“嗟来之食,摇尾乞怜,皆是贱格。”远远站着观摩的赵栋梁也开始变得躁动,一边小声嘟囔着一边回到自己的工位,抽出一本书,转身面对任天富,哗啦啦地翻着。
“就你有骨气你清高。有种你谁的数据都不靠,自己预报。一个神棍。”张勇听清了赵栋梁的话,不由自主地讽刺。
整个气象台里,张勇最看不起赵栋梁。祖上三代都是富商,他自然在看人待人方面颇有天赋。虽然深谙世俗的那一套,但他从不功利和势力,一个小破气象台里也没有值得他功利的人和事。
他一向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专业不好就从不在预报天气这事上大放厥词,端茶倒水跑腿吹水,积极挥能力之内的价值。不像赵栋梁,工作多年没一点成绩,还特把自己当回事。如果不是陈波带头哄着他,估计早就被视为透明人了。
赵栋梁显然不是很服气,他把手上的书往桌上一扣,直视张勇,“我是神棍,陈波就不是了?他撂下一句没来由的话,我们就要忙活一整晚。凭什么?”
“凭我波哥预报竞赛第一,凭我波哥是席,凭……”
张勇反驳的话只说了一半,便被“咣”的一声巨响打断。值班室的门被风吹开了。
|
当呜呜的风不断灌入袖口,把被汗水浸润紧紧黏在皮肤上的布料剥离开时,陈相终于迎着压顶的乌云,骑行到二横巷附近。
这一程虽然辛苦,但整体还算顺利。时间指向12点3o分,根据记忆,这个时候台风才刚刚靠近,他只要向于婶借一辆拉货的三轮车,载着张瑾玥往西边随便走几公里,便可以躲过对地形十分敏感的风暴潮。
这次来得及。
二横巷的样子与他童年记忆里的相差不大。潦草的青石板路窄窄的难以双向过车,路两旁挤满低矮的瓦顶平房,杂乱的电线松松垮垮地从布满霉渍的青砖墙间穿过,偶尔在被油烟熏黑的屋檐下缀下一盏昏黄的灯。
夜里,所有店铺都紧闭大门,一扇扇被桐油强行提亮的腐朽门板后,有的溢出淡淡光亮,有的没有。路面湿漉漉的,车轮轧在上面出粘腻的声音,不小心骑到翘起的砖面上,车铃都被颠响。
这里的夜晚向来寂静,还好有愈加狂暴的风声掩盖,老旧自行车的独奏曲并不那么刺耳。陈相轻车熟路地拐进一个无灯的、只容一人通过的窄巷,那里坑坑洼洼漆黑一片,但他通过得既快又顺畅。这里是他生活了18年的地方,他闭着眼睛都知道该在哪里转弯。
不一会儿,他终于到达目的地。红砖砌成的院墙包裹着四栋三层高的平顶小楼,外墙上刷的红漆还很新,在路灯下反射出水渍的光亮。楼间被粉煤砖砌成的简易花坛隔开,花坛里种着形形色色的植物,其中要数花椒树最显眼,疙疙瘩瘩的树枝疯狂摇晃,在路灯下投出张牙舞爪的阴影。
他把车子停在花坛边,跑向院角的一栋,大踏步迈过矮矮的两层台阶,扑向楼尾的一扇刷红漆的铁门。
“瑾玥,开门。”他边砸门边喊。
门旁边的小窗紧闭着,屋内的光亮被蓝色的薄布窗帘遮挡,比忽明忽暗的路灯灯光更加柔和。他望眼欲穿地期待张瑾玥的身影,可惜没能如愿。正要想办法破窗时,二楼的开放走廊里传来吱嘎的开门声。
“陈波?你没带家门钥匙?”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什么也没摸到。于是后退两步,仰头看见头还是全黑的王奶奶扶着半墙冲他探头。现在她是王阿姨了。
“哎呦,你怎么满头大汗浑身湿刮刮的?快快上我家里来换一件,我家冬冬的衣服你能穿。你家瑾玥我晚上收衣服的时候遇见她了,说是要到小卖部给你打电话。一去去好久。”
眼前的王阿姨顶着蓬乱的头,眯缝着眼睛,语气里满是被扰了清梦的不耐烦,却一直说着关切的话。这让陈相心中升起一股暖意,像是回到了被张瑾玥摇着扇子哄睡的小时候。
“姨你看见瑾玥回家了吗?”他追问。
“没有。你家里一直没动静。”
头顶的话音刚落,天上落下密密匝匝的雨滴。陈相转身小跑两步扶起自行车,踩着踏板准备脚下力时,扭头对还站在原地的王阿姨喊:“姨,一会儿刮大风下大雨还要涨水,你让冬冬弟弟带你往西边去躲一躲。”
哗哗的雨声中,自行车吱嘎吱嘎的声响听不清了。陈相原路返回,穿过已经积上水的窄巷,来到巷口的小卖部。门头上的“二横小卖部”没有被灯珠照亮,两扇木门紧闭着,锈迹斑斑的铁挂锁被风吹得咯噔响。
正当陈相准备再次砸门时,他用余光瞥见不远处还亮着招牌的店铺前,弯弯上翘的屋檐下,站着一个双手举伞的人。伞下,宽大的连衣裙裙摆被风吹得一直飘。直觉告诉他,这是张瑾玥。
没有忐忑,没有激动,没有五味杂陈,当他一路小跑过去看到那张无比熟悉的脸时,心中只剩下焦急。
1点多了,即便这里不如海边开阔,风没有大到能把人钉死在树上,如此之低的地势也注定无法逃脱风暴潮的魔爪,更何况这里还临近南桥河。
南桥河是湛江最大的一条泄洪河道,与同为泄洪河的北桥河共享一个入海口,如果水位暴涨决堤,后果将不堪设想。
“陈波?你回来啦。”张瑾玥看到眼前的雨人,本能地把伞往前递。
陈相接过伞,迎风撑好,一手揽着张瑾玥调转方向,脚步匆匆地走,“瑾玥你听我说,这里马上要洪水,咱们到西边躲一躲。”
张瑾玥没有做声,只是默默跟着。两人贴着沿街的铺面走,走在高高低低木制台阶上,避免了脚下的滑腻。
在此期间,他不断看表,心中也越来越紧张。时间来不及了,他没法将张瑾玥安置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去,只能冒险越过连接南桥南路和北桥公园的小拱桥,爬上公园里的山坡避险。如果桥和公园都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