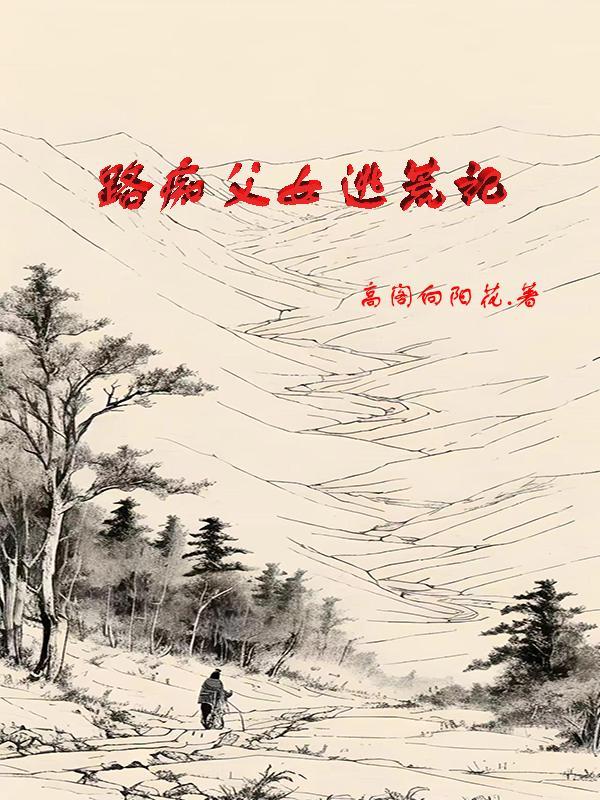极品中文>教渣攻谈恋爱后穿书免费阅读 > 第85章(第2页)
第85章(第2页)
“嗯……”苻缭笑了笑,识趣地没有再提,“近日是没看到他呢。”
奚吝俭沉吟一声。
“清明将至,他有要祭拜的人,不在京州。”他道。
苻缭发觉奚吝俭的神色露出些许倦意,不一会儿又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踌躇片刻,试探地问道:“殿下……也有要祭拜的人么?”
奚吝俭闭上眼:“清明正处在千秋节的时日里,官家不许京州有祭祖吊唁之举,认为那会脏他大运流年。”
苻缭半晌无言。
“其他地方他看不着,倒是躲过一劫。”奚吝俭道,“所以殷如掣这几日离京,清明过后便回。”
苻缭朝奚吝俭靠近了些。
一阵清风吹过,大抵是错觉,他从未觉得奚吝俭的躯体如此单薄,好像有一刹那要被这柔风吹倒,倒在看似一片祥和的美好里,倒在他看似只手遮天而身陷囹圄的无奈中。
“你在轻看孤?”奚吝俭嘴角勾起几分。
“没有。”苻缭轻声道,“只是……”
只是心疼。
他知道奚吝俭不需要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至少不是需要自己的。
他看了一眼小屋的方向,感觉自己正在渐渐离他们远去。
奚吝俭瞥视他看过去的目光,眼底的狠戾一闪而过。
“所以,你能理解季怜渎的作为。”奚吝俭道,“即使他为了自己的目的,不计任何代价。”
“他性子如此。”苻缭应道,“若不是他这样的作风,殿下恐怕也遇不见他,不是么?”
季怜渎在被米阴威胁后,暗自要再寻一个靠山,于是将计就计让奚吝俭发现他,这也是他自己拼出来的一条生路。
奚吝俭该会欣赏这样的人才对。
但苻缭感觉奚吝俭暗含着愤怒,可又不仅这么简单。
“殿下也是如此。”苻缭有些奇怪,“应当能理解季怜渎的想法。”
奚吝俭自己都杀了多少人了。
虽然这朝廷也乌烟瘴气的,但奚吝俭做事毫不留情,目的就是威慑他人,好叫人不敢轻举妄动。
奚吝俭啧了一声,并不满意他的说法。
在于苻缭说的是事实。
他自己清楚得很,可苻缭这样毫不膈应地就理解了季怜渎的做法,让他发现自己并不是绝无仅有的那个。
青鳞和绵羊玩够了,发现主人和恩人还站在原地,不免着急,想催着他们开饭了。
它带着绵羊踢着小石子,一路把零零散散的碎石堆到他们脚边,又用眼巴巴的目光望着两人。
苻缭有些讶异,问道:“这是怎么了?”
“它在生气。”奚吝俭面无表情。
苻缭一看就知道青鳞没生气,所以生气的不是它。
他小心地看了眼奚吝俭。
从奚吝俭试图掩藏情绪的双眸里,他想到了一种最不可能的原因。
但奚吝俭的眼神诱惑着他不断肯定这个推断,以至于瞳孔有些放大,只能倚靠在柳树旁稳住自己的身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