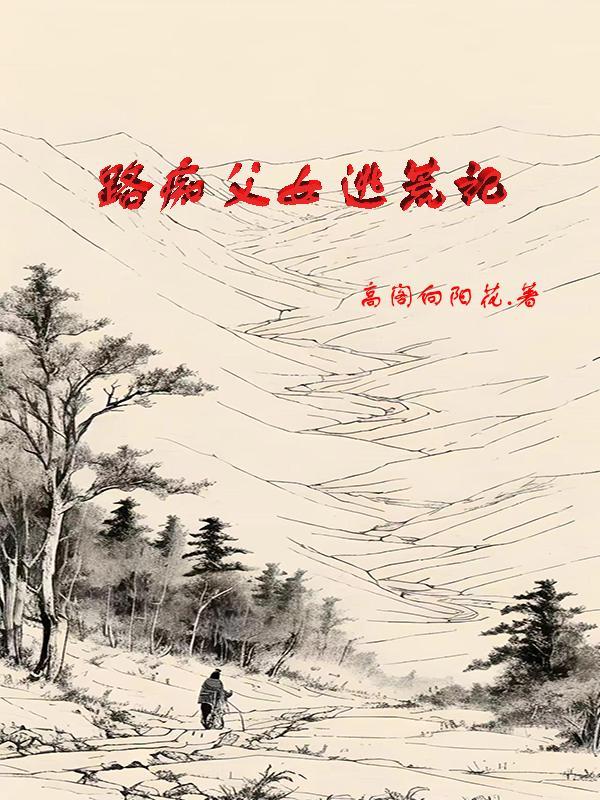极品中文>教渣攻谈恋爱后穿书免费阅读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殿下知道我在谢什么。”苻缭笑着应道。
对季怜渎的态度有所改善,的确让他惊喜。即使知道是他让青鳞受伤,也没有再加罚他。
虽然这样对青鳞不公平。
想到这儿,他又揉了揉青鳞的头部柔顺的毛发。
“早好了。”奚吝俭看它一脸舒服样儿,轻哼一声,“还想借着这个理由躲懒。”
青鳞察觉到主人话里的一丝威胁,抬头望他。
“毕竟是真受伤了,让它多休息几日也无妨。”苻缭不知自己为何要为一人一狼打圆场,想了想倒觉得这情形十分有趣,不禁笑出声。
“既知道它实打实受了伤,为何还能如此体谅季怜渎?”奚吝俭微微挑眉,“你与它也不算生分。”
苻缭眨了眨眼。
“殿下向我说这事,就是想让我对季怜渎失望么?”
如此煞费苦心,不想让自己再挂念季怜渎,也是辛苦他了。
奚吝俭看着苻缭的眼神,知道他又误解了什么。
他不动声色地吐了口气。
“就当是。”他道,“你知道,他想离府有很多方法。那日他已经向殷如掣求情,还要多此一举。”
苻缭有些意外:“这件事我倒是不知情,不过这么看来,殷郎确实挺好说话的。”
奚吝俭捏了捏鼻梁。
“你何时叫上他殷郎了?”他语气里流露出一丝不快。
苻缭一愣,说实话他也记不清了。
“交谈过几次,殷郎觉得先前的叫法有些生分,我便这样叫了。”他眉头微蹙,“可是有什么不妥?”
若真不合适,也没听殷如掣说过。
奚吝俭眼皮抽了抽,没再说什么。
季怜渎的话又在心中回荡起来。
他自己也不明白,本就是个常见的称呼,他也这么叫过林星纬。
……才与他共事多少天,林星纬那脾气他还愿意这么叫。
为何不能……
自然不能。
奚吝俭止住这个念头。
除了身边几个亲信,已经很少人会这样尊重地称呼他了。
但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奚吝俭心中的不快愈演愈烈。
似乎有什么他想得到的东西,被这尊敬的称呼挡在了外面,让他面上看起来风光罢了。
“说起来,似乎没见到殷侍卫了?”苻缭道。
奚吝俭看他一眼:“不必特地换掉称呼。”
“可是殿下看起来很在意。”苻缭察觉了他的异样,“礼尚往来,我也不愿看见殿下不高兴。”
虽然不知道理由,但奚吝俭不是无理取闹之人,改口又不是什么难事。
“孤不在意。”
奚吝俭偏过眼,看见青鳞和自己的食物混在一起,又把目光转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