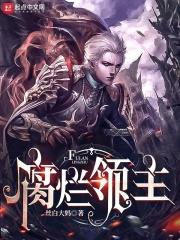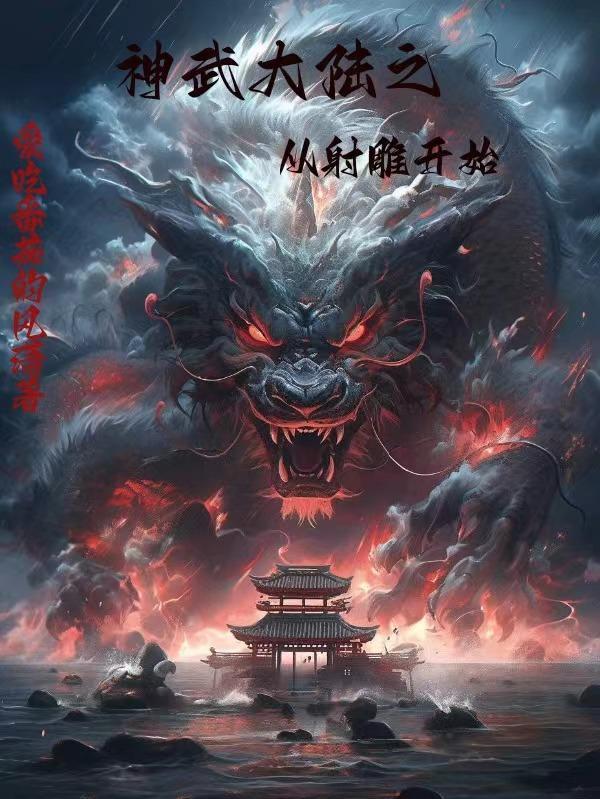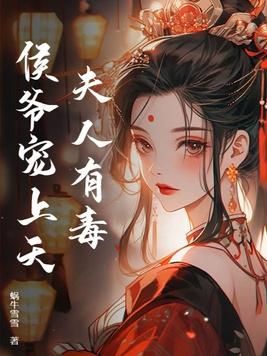极品中文>罗伯特麦基虚构艺术三部曲PDF > PART 2 人物创作(第10页)
PART 2 人物创作(第10页)
当一个人物一无所失时,她便无所不能。
物理背景
恰如生活中所有事物一样,世间的物理力量和时间力量——致命疾病,无法启动的汽车,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某事,路途太遥远无法拿到你所需要的东西——会像双刃剑一样双向切割:阳光能让你享受日光浴,也能灼伤你的皮肤。农场和城市能够提供食物和居所,然后也会用化肥污染河流,并让空气充满毒物。
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斯堪的纳维亚和地中海能养出具有明显不同性情的人。为什么?气候使然。物体能提示意识趋向一个方向而令潜意识背道而驰:在教堂长椅上放一个公文包会给人一种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日本在路灯上装上蓝光灯泡能降低自杀率;洗涤液的味道能让煤矿工人开始注重面容整洁。[3]
在创作一个故事的物理背景时,可问两个方向的问题:(1)我的故事的时间、空间和物体将会如何影响我的人物的人格?(2)背景中的对抗力量将会如何阻遏我的人物的欲望?
社会背景
人物和她的社会会不断互动。社会背景提供各种不同的群体——民族、宗教、邻里、学校、职业。个体对这种群体要么渴望归属,要么意欲反叛。无论是合是离,正是这种群体锚定了她的身份。
例如,“科学家”和“艺术家”这两种文化往往会激发出对照非常鲜明的人格。同理
,南方小镇的居民和北方大城市的市民,幼儿园教师和色情明星,也都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在任何社群的共享特性之中,也会有千差万别的个性。
各种庞大社会系统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他们为成员资格索取的代价。在成功爬上公司金字塔的高端之后,一个经理人也许就变成了一个效率超凡的雇员,却可能很悲哀地丧失了其做人的本分。不过,咱们不要搞错,如果没有帮凶,机构不可能对人性进行完全异化。许多人会暗自欢迎其灵魂的丧失,在一层自欺自慰的外壳内安之若素。想要敲开这层外壳,则需要重锤出击的真诚,而他们早就将这种真诚抛到九霄云外。[4]
正如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故事驱动的纪录片(《高中》《基础训练》《医院》《芭蕾》)所阐明,在机构内工作的人,会不知不觉地互相去人性化。不过,对少数幸运儿来说,他们有时候还能恢复人性。
在创作一个背景时,深刻思考一下其总体文化对你的人物构成的影响,然后规划出你的卡司的具体互动蓝图(见第十五章),到最后,当复杂人物相遇时,以微妙而独特的社会角色来对其进行工笔描摹。
个人背景
家庭、朋友和恋人之间的无可逃避的亲密关系能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生活冲突:朋友之间会欢乐拥抱,直到彼此背叛;一个母亲的爱会像太阳一样照耀
,直到她被忤逆;没有任何事物能像恋情那样快速地爆发为乐观主义或萎缩为悲观主义。由于任何家庭成员都不可能明白的原因,同胞兄弟之间,一个会加入宗教团体,而另一个会成为《美国无神论者杂志》的编辑。他们的争吵会永无休止。
在设置你的故事背景时,务必对卡司内部的亲密关系进行三思。这一冲突层面能够为人物塑造的原创性和微妙性提供绝好的机会。
背景vs人物塑造
一个人物与其物理世界、社会世界和个人世界的各种碰撞能够一点一点地蚀刻出人物塑造的各种特性。若要勾勒出这些背景对你的卡司构成的影响,可以考虑以下八种可能的关系:
1。背景能将一个人物沉浸于家、汽车、工作和扑克俱乐部等事物中,直到她的所有物成为其核心自我的延伸。
在亨利·詹姆斯的《贵妇画像》中,梅尔夫人向她的年轻仰慕者伊莎贝尔·阿切尔解释人物延伸的原理:
只要你作为我而活着,你就能看到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有一个外壳,而你必须认真考虑这个外壳。我所谓的外壳,指的是整个环境的封套。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孤独的男人或女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某种附属物装配而成。我们的“自我”到底叫什么?它始于何处?终于何地?它会溢流为属于我们的一切东西——然后它又会流回原处。我知道我的自我的一个重
大部分就是我选择穿的衣服。我对物质心怀极大的敬重!一个人的自我——对他人而言——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表达;一个人的房子、一个人的家具、一个人的服装、一个人所读的书、一个人所结交的朋伴——这些都是有表现力的。
这个原理曾经为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和乔纳森·弗兰岑的《纠正》等作品提供了创作指南。
2。背景能释放对抗力量来阻止人物的欲望。
在电影《一切尽失》中,印度洋吞噬了一个孤独的水手;在《三块广告牌》中,不公正逼迫一个女儿被杀的母亲去杀人;在《闺蜜假期》中,朋友、恋人和前恋人破坏了一个剩女的周末。
当意想不到的各种反应在一个人物“以为会发生什么”与“实际发生了什么”之间突然轰开了各种鸿沟之后,这些生活表面的断裂会向深处震荡,直至瓦解潜意识。然后,就像火山从地底爆发一样,有害情绪会向上喷薄而出,通常会化为情不自禁、追悔莫及的有害行为。这一从背景向下直达最深层自我的辐射运动便能赋予人物以深度;而从自我深处向上反弹到背景的能量则能汇成一股强大的故事力量。
3。背景及其卡司能形成对现实的一个宏大比喻。
就像是拼图碎片一样,背景和卡司能够无缝拼接;就像镜像对立一样,它们互相定义。人物赋予背景以意义;背景再
反射回馈到人物身上;二者之统一便象征着生活。
在刘易斯·卡罗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奇境”的支配规则是魔法而非物理,其事件遵循的是疯魔而非逻辑。结果是,它的卡司成员,包括爱丽丝,通过经历荒谬的变形来反映其背景——这一切的一切通力合作,便创造出对真人真世以及人性荒诞的一个多维比喻。
背景镜像其卡司,卡司镜像其社会,这一型制在《继承之战》和《寄生虫》中清晰可见。这些讲述分别将“室内剧”与“惊悚类型”进行融合,于是乎人物、家庭和社会便互相感染。他们的故事则反过来反映了真实世界的政治,即腐败成了固着社会的秘密黏合剂。[5]
4。背景会像洪水一样冲刷人物的头脑,送来激流般的物、人和记忆,在她的思想中奔涌:托妮·莫里森的《真爱》和大卫·米恩斯的短篇小说《敲打》。
5。背景会退居后台,将前台留给人物尽情展现。在拉里·大卫的《消消气》和马修·维纳的《广告狂人》中,家、办公室和餐馆似乎仅仅是框定人物肖像的画框而已。
6。背景的存在是那样漠然,那样独立于人物,就像是孑然飘零于一座孤岛:汤姆·斯托帕德的《君臣人子小命呜呼》和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7。背景的物体似乎有其自己的意志:埃德加·爱伦·坡的《鄂榭府崩溃记》和布莱恩·埃
文森的《马群的倒下》。
8。背景的物体变成人物。在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三枚棋子王、后和马,加入一只拟人化的蛋汉普蒂·邓普蒂,填充了卡司。《银河护卫队》中的人物便有类人树格鲁特和被基因工程改造的火箭浣熊。[6]
人物塑造变化
在对付你所创作的物理背景、社会背景和个人背景以及它们所带来的偶发事件时,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便是其各种外部自我。但这些际遇都不是静止的,它们会导致角色的人物塑造发生显著而可信的变化。我能想到的司空见惯的变化方式至少有四种:
1。反叛:一个人物可能会改变她的背景,希望其人格朝她想要的方向发展。乡村艺术家直奔大城市;学者投笔从戎。
2。旅行:国外冒险鼓励的是一种混合的全球身份。青年文化便是一个例子。美国发明、亚洲制造的牛仔裤和网球鞋成了七大洲年轻人的统一着装。
3。时间旅行:一个人物可以躲在一个时间胶囊里。怀旧者喜欢生活在过去;疲于奔命的人生活在未来;享乐主义者生活在任性的当下。[7]
4。互联网:无数网民居住在有地址没地点的电子地理位置上,在其间无际畅游便能彻底改变一个身份。在线文化是即时的,匿名的,没有深度却又是真实的,因为在其中,实际的事情发生在实际的人身上,对他们
进行或好或坏的改变。
外显特性
当你挥舞画笔准备描画你的人物时,你需要强调外显特性,将人物表现为独一的个体。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是现在的样子。所有复杂的人物塑造都要同时呈现先天的基因禀赋和后天的获得特性。基因禀赋(如,音色)往往会终身不变,而获得特性(如,词汇量)却是发展变化的。创造任一特性,必须有成百上千个基因进行互动,而与此同时,它们会吸收无数外部力量的随机冲击。当你通过这两个源泉来调动你的想象力的时候,各种特性便会合并为独一无二、引人入胜的人物塑造。[8]
每一个可观察的特性都坐落在一个从正极到负极递次延展的图谱上。首先是那些公开表现出来的特性,如,世故不世故,爱社交反社会,富有魅力令人厌烦,这些特性定义的是一个人物与熟人和陌生人的关系。然后是在私底下表现出来的行为,如慷慨自私,令人鼓舞吹毛求疵,关心不关心,这些特性标志着人物与家庭、恋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
特性的多寡到底以什么为度?在视觉艺术中,如果一个空白画布为1的话,那么一个完全填满的画布则为2,肉眼能够欣赏的最理想密度为1。3,即总面积的310。我相信,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人物。将主人公的710留白,未知而神秘。基于你所
表达的310,读者观众将会以自己的想象力来脑补其余。因为,如果一个作家要展示一个人物的每一种可能特性,那么讲述时间将会无穷无尽,角色会变得不可理喻,读者观众也会一头雾水。在另一方面,一个单一特性,比如外国口音,又会让一个人物沦为小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