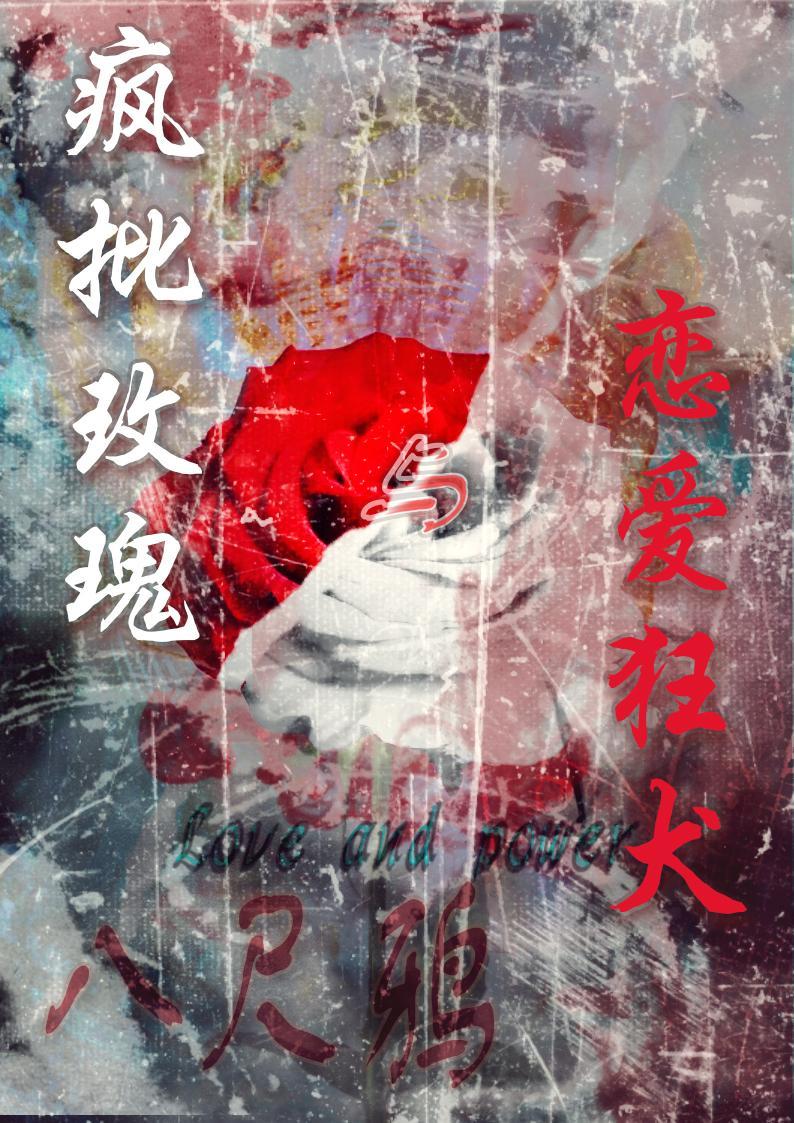极品中文>穿书为师不善 > 第51頁(第2页)
第51頁(第2页)
侍者怎麼可能不明白這個意思?當下拿出托盤裡的白紙欲遞給她。
夏蟬臉色一僵,當即急道:「我妹妹喜歡練武,這白紙就讓給我吧。」
少年掃了她眼,冷笑一聲,不說話。
侍者很有眼色地低下身,將紙往她跟前遞了遞:「小姑娘,接著吧。」
還未等她做出反應,夏蟬就拉住了她的袖子,眼裡淚光閃爍:「妹妹,我不行的,我身子弱,受不住的……」
身子弱?在場中有誰能比重傷未愈的她身子更弱?
她心中一片冰涼,但想起母親閉眼前的叮囑,終是咬牙磕下頭:「我自幼習武,還是更喜歡和刀劍打交道。請殿下成全。」
四周死一般的寂靜。
在場人誰也沒想到她會拒絕,且違背的還是當今太子的意願。
少年盯她良久,最終冷哼一聲,丟下一句「隨你」,轉身離去。
屋子只剩幾個侍者和她們姐妹二人。夏蟬拿著那張白紙,正抱著她哭。
她看著那仿佛劫後餘生落淚不止的女孩,清楚母親的遺願她已經做到。接下來……便是誰也不欠了。
之後,她進了殺手營。在入營當天,他為她取了名字——風殘月。
她不明白為什麼其他殺手的代號不是動物就是只有兩個字,比如「夜鶯」和「黑風」,但她卻擁有一個有名有姓的名字。
有些像人。但殺手……不是不能像人嗎?
有了人意識的武器,便不由自己控制了。
她不解,卻不敢問。
入營時教官對她說的第一話就是:主子的話不要問,主子的命令只管照辦。
她將滿心疑惑壓下,恭敬接受。
再之後,她們該習武習武,該調教調教。學成之後一個拿起劍,一個端起茶,共同為一人賣力。
許是當殺手當久了,用那個名字用慣了。現在的她只記得自己叫風殘月,至於以前的名字……她早忘了。若不是夏蟬一直活著,她怕是連「夏」這個姓都快記不住了。
夏蟬總是「阿月」「阿月」地叫她,她有時會好奇她叫的是現在的「風殘月」,還是在叫她以前的名字。她已經不記得自己名字里有沒有「月」這個字了。她想,如果自己去問夏蟬,她估計也不清楚吧。
那個名字,似乎真的隨著時間的長河遠去,包括自己在內,再無人記得了。
「為什麼你的姓包含在他的名字里,而我卻沒有這份殊榮?」
夏蟬越說越氣,顯然已被嫉妒沖昏了頭腦,不顧形象在殿中手舞足蹈。
「都是一同攔的車,一同入的宮。同樣都是伴他身側,甚至你陪伴的時間都沒我多,憑什麼他就這麼在意你!」
「這不公平!」
「公平?」
風殘月聽了簡直想笑。
或許是愧疚吧,自那次人生抉擇後她因傷得太重需養傷,暫緩了進殺手營的時間。在那段療傷的日子裡,夏蟬除了完成每日調教訓練,都會抽出時間來給她煮粥熬藥聊天,也算細心體貼。除此之外,她還會時不時抓個蟲子摘朵花來讓她開心,甚至還偷偷當掉自己身上的飾,為她買了幾本書解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