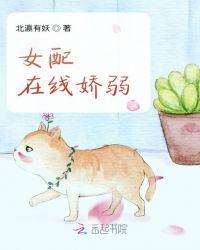极品中文>踏神界逆九州 废物七小姐权倾天下 > 第83頁(第1页)
第83頁(第1页)
他換了個姿勢坐,問道:「昨日北邊來信,葉老將軍頭疾復發,朝廷想調祝勇掛帥來著?」
謝緒風道:「是。」
沈子梟斂了斂眸:「祝勇是大哥的人,他不能去。」
孟願恍然抬頭:「殿下的意思是……」
「朝堂之上權力傾軋,波詭雲譎,你說這背後之人,貪這麼多銀子做什麼?」沈子梟吹了吹茶水上的兩片茶葉,問道。
眾人皆是一怔。
大殿裡陡然安靜得針落可聞,唯有外頭的鳥雀嚀鳴聲不時傳來。
陽光透過薄薄的窗紙傾瀉下來,空氣中浮動著許多細小的塵埃。
謝緒風眉頭顰蹙,幾乎是一口氣提到了喉嚨里,堵住了。
許久才說道:「難道,有人在私自屯兵?」
孟願驚得差點從氈墊上跌到地面去。
另外兩位大人,亦是惶然說不出半個字。
偏偏處於風暴中心的沈子梟最是淡定,啜了一口茶水,道:「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想起兵造反?那也要師出有名才行,否則如何堵住天下人的悠悠眾口。」
他把茶盞擱下,「啪」的一聲穩穩放在桌面,同時掀起眼皮看向眾人:「而我等要做的,便是守住這份『名正言順』,讓天下之人信服。」
「所以無論蔡君充背後之人是否為恭王,此次對巒骨用兵的軍功,殿下是要定了。」謝緒風說道,「正如為安陽百姓和那些鹽礦工人剜除毒瘤,您勢在必行。」
沈子梟深深看向他。
眾人都靜默許久,這時忽然有人大著膽子說:「可是這樣未免更被陛下忌憚。」
謝緒風朗月清風一笑:「黃大人還是沒有看清嗎?饒是殿下什麼都不做,只在東宮聽曲賞花,咱們的陛下還是一樣會忌憚。」
只因沈子梟處於的位置,本就註定要腥風血雨。
也因崇徽帝所在的位置,本就註定要猜忌多疑。
沈子梟還未聽完謝緒風的話,就已經在心底喟嘆了一聲——
謝逍啊謝逍,你那平和溫煦的雙眸下,藏著怎樣熱忱的火炬。
他素有「雪無暇」的美名,看上去是多麼凡脫俗之人。
可沈子梟知道,他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卻並非對世事冷漠;雖清風霽月,卻並不願將自己困在那一隅之地獨自安穩。
生於簪纓世族,他從未辜負這一襲官袍。
沈子梟與他對視一眼,什麼都沒說。
但是這沉默已抵過千言萬語。
他又對其他人道:「孤會向父皇請命出征,此事屆時再仔細商議。至於蔡君充,凌遲處死,諸子於朝中有職務者斬,年十四以上皆戍邊關,親屬給披甲人為奴。許懋濡重杖處死,其餘親屬沒入官奴。其餘人你們看著辦吧。」
聞聲,眾人紛紛起身告退。
唯有謝緒風,待所有人都離開之後,獨自留下。
沈子梟知道他有話要說。
於是摁了摁鼻樑,搶先一步制止他:「什麼都不必講,你去吧。」
謝緒風頓了頓,只好離開。
直到踏出門檻,他掙扎之下,還是轉過了身,用幾近嘆息的聲音說道:「無論何時,殿下身邊,還有謝逍。」
沈子梟僵在原地,連同呼吸,都凝固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