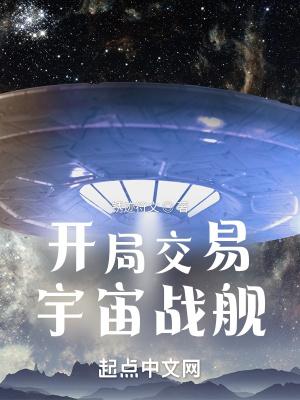极品中文>奇兽异物的意思 > 多闻(第2页)
多闻(第2页)
坐在马队车尾,与一位资历老辣的镖头并驾齐驱的福生,循着视线抬眼望了望不远处已经能看见密集之外隐约有城市踪影的远方。
从神皇派给他的消息里,靠近山南道便能瞧见城上气运,当然,这得是专门的望气士才能看见,一般道行高些的其实也会有所觉察,但向来都不够准确的。
远处,天空中,斑驳的雾气似云雾,朦胧缭绕好似一口大煮锅上飘荡的香浓气味。与此同时,在白的缓缓出光亮的透明雾气外,隐约有一层墨绿色的罩子,时隐时现的笼罩在白雾之上。
“咱们这老些年没在草地上跑过马了,当年前帝还在世的时候,咱还一口气从辽北打到当涂以西的,如今,诶…”身旁,那粗嗓门的汉子夹着马鞭,自顾自向着福生说起他那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以上内容,福生也是听了少许,但奈何这位年岁估摸有近五十的镖师,一说起话来,那是一个滔滔不绝,恨不得把他这辈子所有的高光时刻都抖擞出来。
要是换作平时,福生倒也乐的当个故事,但自靠近隋城,他便越的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不同于以往,福生能感受到周围灵气出现了明显变化。先是浓度提高了,一般而言灵气的浓郁程度对事物的影响是利弊参半的。
往好了说,人在浓度高一些的灵山宝地里待着是会延年益寿,身体强健,但坏处也很显然,这种地方如果没人保护是会引来一些不小的麻烦。
更何况,这里的灵气还不像是神皇派所在的仙山,是纯正浩然的正气,反而沾染了阴寒,人长此以往吸入身体里会诱各种疾病。
福生无声无息间开启了神识,在凡人眼中,对于道人开天眼,开神识其实也都是察觉不出什么的,除了个别灵感颇高的除外。
而透过那双凡人看不到的纯白眼眸,福生现,空中时不时会漂浮着一些微弱且细小的绿色斑点,就像蒲公英的种子,在空中摇晃,密度不高。
顺着那些光点移动的痕迹,福生在地上的草丛里寻找,这一瞧还真让他看出了点门道。
只见一朵娇嫩的红花躲藏在无数多枯枝泥泞里,它的花朵尚未张开,鲜红如血的花苞如同一颗露在地面上的种子,安静的躲藏在旁人无法注意的阴影里。
福生眼眸渐渐变得有些凝重,周围的视野随着他的神识扩散,而开始放大。
十丈,百丈,千丈。
福生灵感忽有触动,在离他们尚远的森林内另一个方向上的官道处,一股阴风吹过。
一瞬间,那种熟悉的感觉充斥脑海。
“不好意思,小道突然想起来一件私事,就先先行一步,前方不远便是隋城,诸位有缘再会!”
不等其他人询问,福生架马往前行去。
众人的声音渐渐被他抛之脑后。
此刻,策马在树林里的福生神识一刻不停的锁定并确认着之前的位置。
两年,已经过去了两年之久。
从他被击溃的那一晚,在面对师傅的亲手一剑,他那一颗炙热的心,便从此有了燃烧的理由。
森林深处,从阴影里走出来的三个着黑衣,头戴兜帽,但依旧有狰狞白光从隐藏的帷幕之下显露,反而越使得恐怖。
此三人,为一位手持鬼头大刀,肩上扛着一具不完整的尸体,而身后二人则分别拽着手脚等其他物件,看起来与恶鬼无异。
就在三人打算做些什么的时候,丛林外,马蹄声由远及近。
“来人了?”一位戴面具的转过身子,他面容呆滞,嘴角还流淌着腥臭的液体,看起来并不聪明。
另一位成员刚要开口说些什么,但见前面转头的那位,身子突然往后退了两步。
就在他歪着脑袋,准备过去查看时,那家伙浑身一抽,随即整个身子在肉眼可见的度下膨胀,接着嘭的一声炸开。
在惊愕之余,率先反应过来的是那拿着鬼头大刀的,只是在那家伙准备起身的一瞬间,一条雷霆从那膨胀的同伴身后蹿出,直奔他而来。
躲闪不急,雷霆触之,大刀在一阵噼里啪啦乱响里,脱手,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出,便冒着黑气,整个身子被雷霆击溃,化为飞灰。
这一切都生的太快,太突然了。
耳边甚至才听到那轰隆隆的雷鸣,伴随着莫大恐惧,甚至忘了,之前听到的马蹄声,如今也已快至身边。
“你是谁的部下?”
站在他身后,福生将一张写有镇字的黄符贴在这名鬼差的脑门上。他的声音很寡淡,寡淡到似乎多说一句都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我是…”那名鬼差咽了口口水,他脸上的表情罕见的浮上了极多惊恐。如果他能看见自己的脸,想必,就会现,这上面的表情,和他在很多临死前的人们脸上看见的,一模一样。
“我是喜夜王手下,责令巡视的阴差。”他的声音颤颤抖,浑身因为头顶的符箓而不得有丝毫动作。一边,寄希望于这位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一边又在想回去之后怎么通知上面,好将面前之人碎尸万段。
就在他思绪百转千回之际,蹲在他身后的福生将黄符朝下一摁。顿时火光冲天。
而被这突如其来的阴火灼烧,但身子,甚至连声音也无法出仿佛依旧被禁锢着的阴差来说,眼睁睁看着那个蹲在他背后,一点点缓慢消失的身影,这时,他才回想起,死亡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喜夜王,原来是笑判官的手下。”已重新站在官道上,身旁迟来的马匹在靠近福生时缓慢停步,极有默契的站在离他最近的地方。
摸了摸相处有段时间的爱马,福生的手一边捋着马背上的鬃毛,一边在脑子里电转火石的规划着接下来的行动。
隋城门口,侍卫脸上都带着些浓重的黑眼圈,似晚上没睡好般。
他们依次检查了车队上的人员和货物,在反复确保没问题后,才让人通过。
其中碰,一位打了个哈欠,他揉着眼睛,靠着城门旁的土墙,抬眼看了看远在地平线上头的太阳,嘟囔道“终于又要熬到天黑了。”
城外,又是孑然一身的张福生,独自一人从树林里走出,他站在树下的阴影里,望着城门方向又看了眼旁边孤零零的城头,随即挑了下眉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