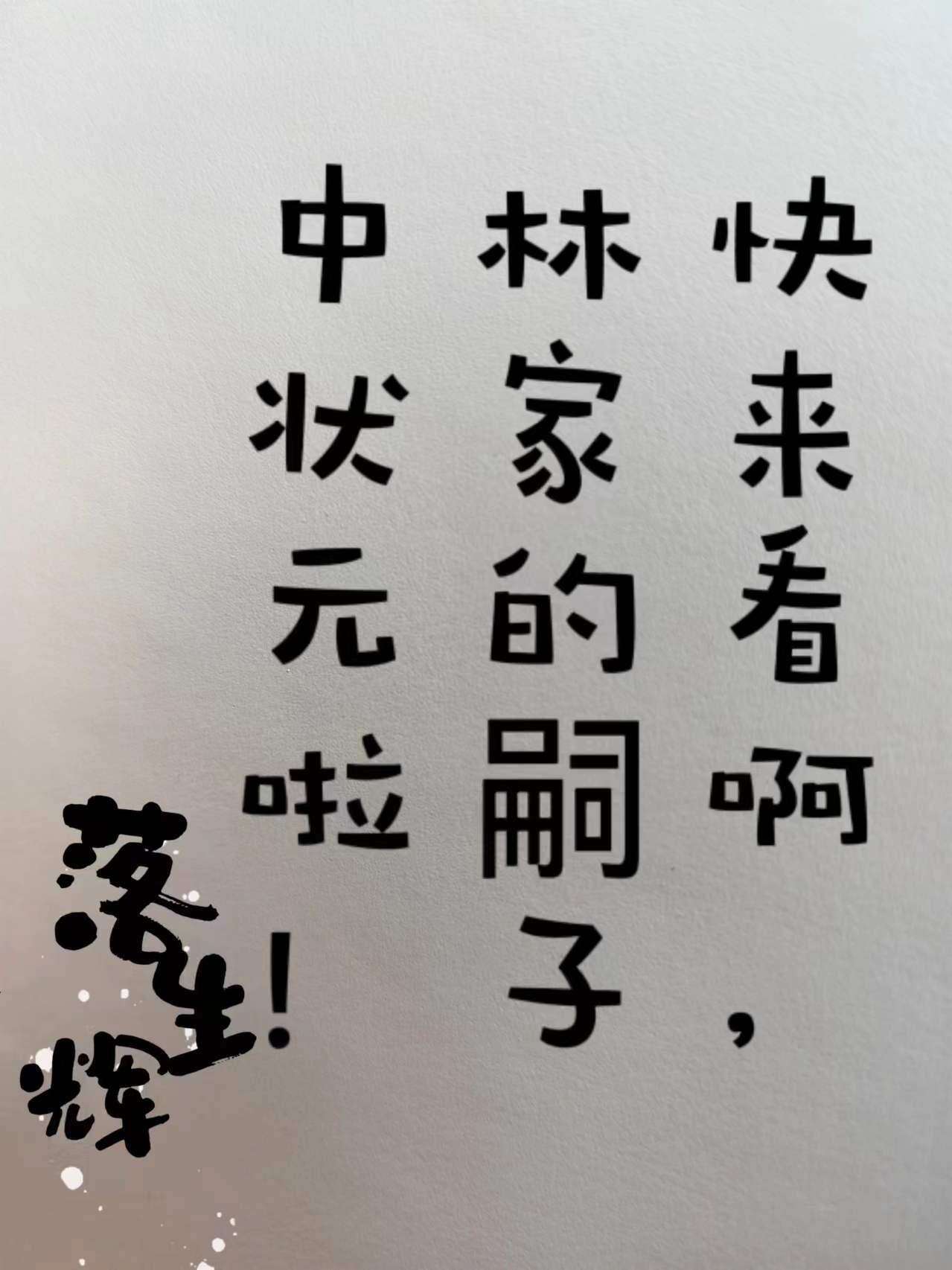极品中文>穿成农家大反派 > 第一百九十一章 似是故人来(第1页)
第一百九十一章 似是故人来(第1页)
赵谦一脸惋惜:“季萧身子弱,盖城楼的罪许是吃不消,也是入秋后现染上肺痨,大夫说他已病入膏肓,深秋时咽气的,已经埋土近两月,就埋在前面不远处,安公公若是想去,属下可以带您前往祭拜,就是怕冲撞了您。”
安公公顺着赵谦的手指望向远处的坟头包摇头叹息,真是人死如灯灭:“罢了,皇后娘娘的差事要紧。”
当年太子一案季萧是拿自己的命为蝼蚁的平民申冤,可是最后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被贬流犯村?
从那时起,他就知道,陛下要的从来只是顺从的大未子民,当年和章桀将军想要的太平盛世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安公公随着赵谦走向另一间房子,离得挺远的,走得他双脚都麻了,有些责怪人家也不晓得安排马车。
房子在一里外,离得近了就能闻到药气,屋外有个脸上蒙着白布的老郞中将熬好的药端进去。
麻风病是五损五衰的恶疾,还会传染,安公公可不敢靠太近,只是站门口远远站着。
小喜子早吓得脸白,深怕被染病,比安公公躲得更远一些。
里面的咳嗽声传来,安公公不自觉的往后退了退,四下打量着屋子,是新盖的茅草屋,屋里的陈设很简陋,只有床、桌子和恭桶,屋里四周倒是备着炭火,其中一盆烧着艾草,满屋的烟呛味。
安公公蹙眉,闻到那烟呛味又不自觉的后退几步,小喜子早就退出百米远。
屋里的父子两全身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只能露出一双眼睛,另一个小孩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偶尔出几声咳嗽。
正如赵谦所说,安公公根本认不出来,二皇子何等清风霁月的人儿,不过三年的功夫,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小皇孙那样虚弱,只怕也是时日不多了。
“公公不进去吗?”赵谦问道。
安公公叹息:“给二皇子留个体面吧,咱家突然出现也是伤他的心。”
赵谦候在一旁,没有再说什么。
大夫此时走出来,卸下脸上的白巾,年迈的脸上满是惋惜:“可惜在这个时候作,不然也能恢复得快一些,还请赵大人多添些炭火。”
赵谦点头应下:“有劳李大夫了!”
李大夫背着搭链朝安公公和赵谦作揖后转身离开。
安公公听大夫这么说,脸上的惋惜更加明显,心里冷哼,如此一来,陛下就算想对二皇子有什么想法也不能了。
“赵监史,既然皇后娘娘交待咱家的差事已办好,咱家也该回京都复命了。”安公公对赵谦道。
赵谦拱手:“公公周车劳顿实在辛苦。”
这时,一名差役前来对赵谦急色禀报:“赵监史不好了,那个禾慎突然吐血,怕是不行了。”
赵谦神色微变,朝安公公作揖后疾步拦住李大夫。
李大夫知道后赶忙让赵谦带路。
安公公神色未见波澜,人啊就是不能存着不该有的指望,否则,万念俱灰皆在一念之间。
也罢,就当全了禾慎和陛下的君臣之谊,若是陛下问起他,是死是活也能给陛下回句话。
禾慎已经被安置在塌上,嘴角腥红,屋里的血渍被赵谦让人清扫,但血的腥气还在屋内散开,一时浓腥得让人作呕。
同住屋里的流犯看着随时咽气的禾慎,神色未见动容,这种事情,见得多了也就麻木了。
李大夫铺开布囊施针,在禾慎身上几处要穴下针,针法极妙,一共下了十针,不稍片刻禾慎幽幽转醒,气若游丝的喃喃自语:“陛下,臣对你是一片忠心的啊,你怎能弃臣不顾啊……”
李大夫见人醒了,对赵谦道:“大怒则形气绝,若处置不好怕是会半身不遂,赵监史还是派人去我那里抓几副药给他服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