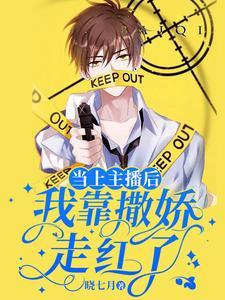极品中文>何不同舟渡晋江 > 第43章 除夕夜(第2页)
第43章 除夕夜(第2页)
唐戎将木匣子放在桌上,打开,里头码着整整齐齐的白银。
甘棠夫人将木匣子推给谢却山:“这是一些酒菜钱,谢三,你拿去分给你的岐人兄弟们,让他们也好好过个年。”
言下之意,却是在说,这个年,让那些岐兵们都滚出望雪坞。
谢却山顿了顿。
这木匣子上刻着沥都府钱庄的招牌,分明是甘棠夫人回府前刚取的。银票不好分,而银子是实实在在的财物,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岐人拿了钱,就得撤出去。看来她早就想好回来的第一件事要做什么了。
在她来之前,谢家没有敢这么做的人,或者说,没有这样拉得下脸又站得住立场的女人。6锦绣膝盖太软,见风使舵,谢穗安性子太烈,不愿服软;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至于南衣,根本不是个能话事的。
“有问题吗?”见谢却山不接话,甘棠夫人抬眼一扫。眉眼还含着笑,语气却重了几分。
大家都屏着呼吸,想看谢却山的反应。
“二姐,这不大好办。”谢却山十分恭敬。
“所以才叫你去安排。”声音十分笃定。
“……好,二姐。”
南衣惊得下巴都要掉了!这还是谢却山吗?他连亲爹亲奶奶都敢忤逆,却对这姐姐毕恭毕敬。
这难道就是血脉压制?
是的,谢却山从小就怕自己的二姐。
谢却山幼时也是调皮的,谢钧无心于他娘亲,对这个儿子自然也不太重视,偶尔想起来,便要雷厉风行地教育一番,方能显示自己的权威,但这对谢却山这个一身反骨的人来说效果甚微。
唯独在长他六岁的二姐面前,他不敢造次。二姐从不出错,识大体,懂规矩,却又没有寻常世家女子那般迂腐胆怯,做事极其大气。她对家中弟妹做的赏罚,公平公正,叫人心服口服。她要只要一沉眼,几个调皮的弟妹就立刻知道分寸。
这份敬重是刻在骨子里的。
哪怕今日,谢却山都不敢不听二姐的话。
谢家众人心里都是窃喜,总算有人能制住谢却山这个魔头了。
不过南衣隐约觉得,甘棠夫人的忽然归家,没那么简单,也许这背后还有深意。
——
这个除夕夜,众人一起用完晚膳,又热热闹闹地聚了好一会才散去。
谢却山用了几口,便早早走了。他不在,大家才能放松。
南衣也在席间告辞回房,这谢家家人团聚,跟她也没什么关系,她干坐着只能无聊。
回到房中,南衣看到案上放着一个托盘。
托盘里装着一套新的衣裳,抖开一看,里装是鹅黄色短袄,料用得极其厚实,对襟上绣着百菊纹,下装是一条绣着点点白梅的印金百迭裙,外头还配着一件领口袖边都镶着毛的白色长褙子,通身用的都是绸缎。
南衣雀跃起来,她平日里穿的衣服是6锦绣从谢家库房里随便挑出来拿来给她的,虽然够保暖了,但多少有些寒碜,这套衣服却是花了心思的,也是她的身量。
她料想这种女儿家的东西是谢穗安送的,可再打眼往托盘上一看,底下还压着一叠宣纸字帖。
字帖的开头是他力透纸背的遒劲字体,南衣只看得懂后面三个字:年、快、乐。
头一个字猜也才能猜出来,是个“新”字。
南衣惊了,除了谢却山,还能有谁?
他竟然还记得她不舍得丢掉一件沾满血的衣服,在除夕之夜给她送了一套新衣服。
“新年快乐。”
他隔着纸笺对她说。
南衣捧着衣物,埋头进去深吸了一口气。
是新衣的味道,还熏过了上好的檀香。她又仔细闻,试图闻出一丝从他手中经过的味道。
她总觉得是有的。
南衣很开心,在这辞旧迎新的夜晚,竟生出一种有了着落的错觉。
可当她的目光无意间瞟到桌上摊开的佛经,一丝沉重又浮了上来。
她昨夜认认真真地比对完所有的字迹,确定了望雪坞里的细作就是乔因芝。今天她没来得及告诉谢穗安,只能明天再同她商量对策。
在此之前,她观察着望雪坞里的人,有鬼祟的,可疑的,她都怀疑过,但她根本没有想过会是这个人。
她旁观着她对谢衡再逝去的思念和哀伤,所有人都在忙碌着新的生活,只有她走不出来,守在槐序院中。她只是一个妾,并没有人在意她过得如何。
所有人都相信她很爱谢衡再,南衣也深信不疑。
如果乔因芝不爱谢衡再,怎么会对南衣有如此大的敌意?这敌意是自内心对夫君的维护,绝非逢场作戏。
可偏偏就是这张深爱的面具之下,是一个无情的谍者。是她出卖了谢衡再最重要的计划。
南衣甚至敢说,谢衡再的死也跟她有关系。
人人面上都一张皮,贪嗔痴怨,藏在内里,她能看到的,不过是水面上的千万分之一。
想到这里,南衣刚热络起来的心就平静了回去。
谢却山这样铁石心肠的人,就算偶尔给她一些恩惠和怜悯,恐怕也只是一种收买,做不得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