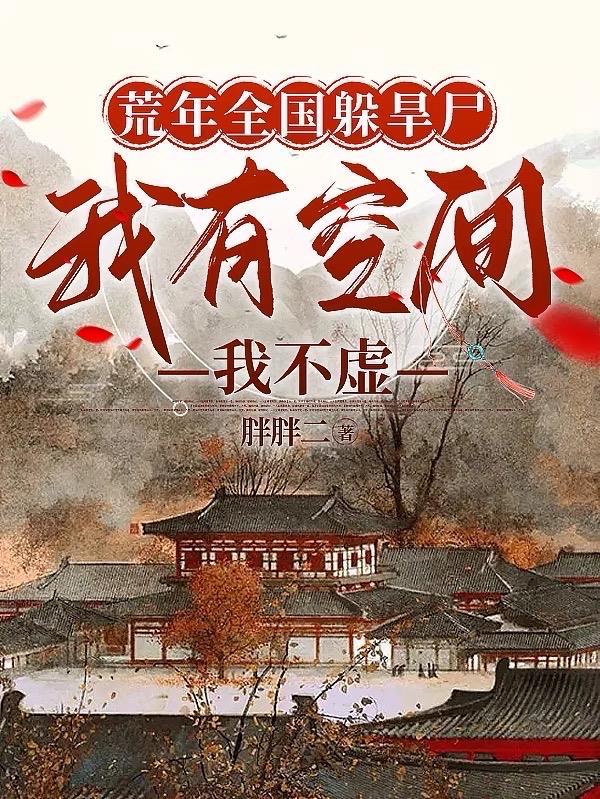极品中文>佞臣似朵娇花全文免费阅读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霎时间群鸦惊飞,金铃叮当作响,就连候在屋外的薛富贵也不由颤了下身。
「陛下还在为虞大人的事发火?」
小福子咽下口唾沫,擦了擦额前被惊出的冷汗,上前问道。
这次薛富贵倒是没骂他多嘴,伸出根枯木一样的指头,指了指灰蒙蒙的天,唉声叹气道:「圣心难测啊。」
太华殿内,庆延帝坐在榻上,身前摆着张乌木方桌,桌下跪着名身着朝服的武将,一副钢筋铁骨,宁死不屈的模样,想必是自下朝起便在此处僵持不下。
「起来!」庆延帝向他喝道。
杜云轩眉头紧锁,抱拳道:「臣罪该万死!陛下若不答应,臣」
「你也知道罪该万死!」庆延帝打断他,重重一掌拍上乌木桌,怒不可遏道:「你到底还要朕如何!他明明不是二哥的孩子,你丶还有皇后,你们还要逼朕到什麽地步!」
杜云轩腰板笔直,头却始终不肯抬起来,垂首沉声道:「盛年待珵美如己出,你不该折辱他,折辱了他就是折辱了虞家,」说到此,他愤然抬头,目光如炬瞪向高处的庆延帝,一字一句道:「你是在恨,这麽多年,你始终没放下。」
庆延帝的身体微不可察地颤了颤,那是一种汇聚了愤怒丶惊慌,以及被人看穿到心底最阴暗处的无措。
当年便是,三人中,自己这个大哥总是能一眼看穿他的心思。
杜云轩是照耀着众人的太阳,而虞盛年是刚正不阿的树,只有自己,是活在阴沟里的一株毒草。
唯有豁出命似的爬,才得以见到片刻阳光。
一个人如果活得太狼狈,就难免心生怨憎。
就比如他恨急了自己那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两人明明是前後脚出生,凭什麽他就是大的而自己是小的?
凭什麽在大皇子病死後,哥哥可以继承太子之位,而自己不能?
明明他是那麽软弱无能,全身上下唯一的优点便是脾气好。
只因为福禄寺的和尚说他慈悲圣明,而自己一将功成万骨枯,就这麽被踢出了太子之位。
慈悲?
可笑。
慈悲可保江山社稷?还是能救万民於水火?
桌後,庆延帝深吸一口气,带着些颤抖问道,「大哥,当年你又为什麽要帮我?」
杜云轩似有所触动,沉吟良久,答道:「阿仁,你是个好皇帝。」
庆延帝听罢大笑起来,摇着头道:「杜云轩啊杜云轩,你还是同从前一样自负,也难怪当年二哥会被你逼死。」
杜云轩不为所动,虞盛年的死带走了三人过往的一切,情谊也好,抱负也罢,留下一地残垣,无人再拾得起来。
多少年前,扬州城里落花飞絮,不受宠的皇子骑着匹瘦马,载着心爱的姑娘,左右挚友相伴,穿过细风斜柳,跨过无际银涛。
那一年还不是将军的他,牵着同样还不是臣子的另一人,十指相扣,紧得容不下一丝缝隙。
芦絮作雪,鸥鹭惊飞。
说不得是谁压了谁的衣带,唯有人错愕後扬了扬嘴角,黑瞳如墨,倒映出彼此身影。
而後便是解衣抱月,低吟蹙眉,杳杳间吹灭一天星。
一番风雨,一番狼藉。
年少的荒唐总能在沉寂过後直插心房,令人叫苦不迭。
庆延帝面色黯然,盯着跪在地上的杜云轩,目光中无不讥讽地道:「大哥,听我一句,你若心疼他,给他些钱财宅邸就罢了,唯独不能当儿子养,他是匹白眼狼,什麽都好,独独没有心。」
第18章
时近晌午,宫人们都开始偷懒,小福子老远就见一穿着白色袍子的人一瘸一拐朝太华殿这边跑来。
腿脚虽是不灵,跑得倒很快,不多时到了眼前,这才看清原是虞珵美,赶忙朝他挥了挥手,意思是不要过来。
虞珵美停在门口,直到小福子走近,才不解道:「陛下不在?」
「在的,」小福子也是小跑而来,喘着道:「但陛下说,说了,要是虞大人来,就,就让你回去!」
虞珵美疑惑,「他不见我?」
「不见,」小福子点头,继而向虞珵美靠近了些,压低声音道:「陛下刚才与杜将军发了好大一通火,杜将军走後就谁也不见了。」
这下虞珵美更加想不通了,思绪在脑海里游了一圈,心道:「不见就不见,正好老子还没想出怎麽把昨晚的事糊弄过去,这会儿进去难保不会屁股开花。」
「多谢公公了。」他向小福子道谢。
小福子摆摆手,「虞大人客气了,咱们本该互相照应才是。」
这话说得虞珵美一头雾水,小福子才来不到一年,他们还没熟到这般地步才对。
仔细端量小福子的那张笑脸,这谄媚劲儿自己可再熟悉不过,当即有些恶心,懒得再细想。
他还有好些事要做,交了腰牌出宫,直奔东城,来到一处高大阔气的宅院前,由仆人通报,将他引到了范德尚房中,他向这位和蔼可亲的首辅大人将昨夜的事大概讲述一遍。
范德尚捋着胡须不怒不恼,犹自笑得意味深长,忽又想到什麽,向虞珵美道:「去见过陛下了?」
虞珵美摇头,疑惑道:「不知怎地,陛下不见我。」
范德尚脸上的笑容更甚,起身来到他身前,负着道:「知道陛下为什麽不见你吗?」
虞珵美的眸色一沉,「小的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