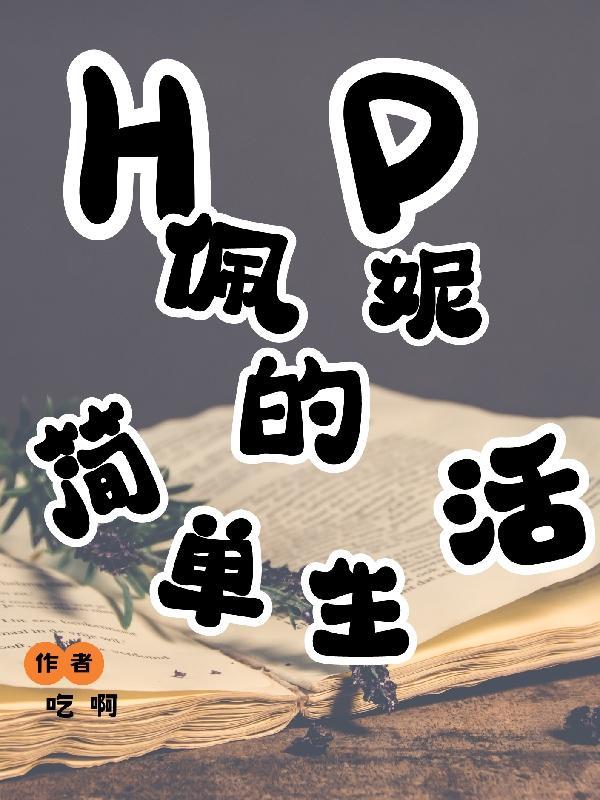极品中文>画耳朵怎么画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除此之外,她自学画画以来没认真画过人像,包括简笔画。
她说了声抱歉,拒绝上钩。
何斯屿眉尾轻佻,又抛下鱼竿,“你给我画一幅,我出钱买下整条街的酒。”
在座的除了贺锐泽,其他人都觉得何斯屿就是个为了把妹无底线装逼的狂妄自大的小伙子,但不免有人起哄凑热闹,瞬间,周围都是劝姜早答应的声音。
姜早迎上那双半眯着的眼眸,突然笑了声。
何斯屿歪头,“你笑什么?”
她之前也会图一时痛快,买下整个商场的衣服、首饰。
当然,她不会在其他人面前暴露以前的自己,以免有人笑她此时此刻的落魄,她摇摇头,没说什么。
他不依不饶,“画不画?”
按照何斯屿的秉性,如果姜早不答应,他真的会一直纠缠下去,半响,她点头做应,鱼儿还是上钩了。
见此,何斯屿二话不说就跑开,在每个卖酒的摊位停有三四分钟,饶了一圈,回到原点时,累的满头大汗,汗水从额头顺着流畅的面部肌肉留到下巴,姜早没有多想就站起来为他擦汗。
没有摊开的窄小正方形纸巾给足了空间,她那无处伸展的指尖总会时不时的触碰到他的耳垂,就像到处留情的蜜蜂。
何斯屿痒得不行,抓住她的手,慌乱地阻止这场无声的调戏。
“痒……”
姜早愣住,抽出手假装镇定地扫了一眼一旁的言舒然,再看向何斯屿,“你们一起吗?”
“一起。”
“只画我。”
两句话几乎是同一时间说出来,言舒然是前一句,后一句是何斯屿说的,态度坚定。
姜早有些搞不懂了,都快处成情侣了,为什么他不乐意和她一起入画。
因为姜早再次提起画笔,京音今天高兴,她拉着言舒然笑道:“何老板出手大气,舒然妹妹你过来,我帮你画。”
虽然言舒然很想和何斯屿出现在同一幅画里,可就算她的眼睛都快黏在他身上了,他依旧像个不知情的人一样,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眼里也只有姜早一个人。
如果不是因为喜欢,没有一个成年人会愿意为一个人买下一整条街的酒。
言舒然也不傻,别人能看出来的她也能看出来。
她笑着走到京音面前,摆出微笑,但此刻她的笑比哭还难看,京音傻乎乎地出声提醒,“妹妹,你还是别笑了吧……”
姜早这边更是尴尬,她盯着一排画笔看了很久还是没有想好要怎么把面前这个人高马大的男人画下来。
好在何斯屿没有摆什么有难度的姿势,也没做什么表情,不然他肯定会再一次毒舌,diss她是活化石。
“坐着的人果然不会腰疼。”何斯屿闲悠悠地说了一句,实则是在埋怨姜早是故意不动手,让他一直站着。
姜早抬头,忽的捕捉到那双杏眼里一闪而过的星光,她闭上眼,幻想着何斯屿在大学,在出事之前抱着贝斯在舞台上无限发光发热的模样,最后想到的是他方才提在手上的比他的脑袋还要大的向日葵,灵感慢慢涌现。
她分别挑出黄色、棕色、绿色的水彩笔,刷刷两笔就把一朵鲜亮的向日葵画好,再拿起一根黑色的,思考了两秒才下笔。
何斯屿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逐渐有色彩的白纸看,在看到姜早将他的头画在向日葵右边连着花瓣时起了好奇心,他抱着手认真地等待她的下一次落笔。
两分钟后。
“画好了。”姜早放下笔,吹了吹上面的墨,她忐忑地将人生中的第一幅人像画交了出去。
何斯屿接过画,将其反过来,一个高站在舞台,靠着向日葵大笑的少年闯入眼帘,少年的脸紧贴着向日葵,长过眉头的刘海都没能遮盖他这个年纪该有的野心,仔细一看向日葵里的几颗瓜子跑到了他的脸上,为蓬勃增加了一丝调皮。
姜早见他傻楞在那,小心翼翼地问道:“不满意吗?”
何斯屿挑眉,眼底眸光微转,“不像。”
“这画有我的幻想色彩在,如果你不满意,我可以再帮你画一幅。”
他直勾勾地看着她,忽地笑了,“幻想色彩,在你的精神世界里我是这样的?”
她的回答没有迟疑,“嗯。”
何斯屿突然弯下腰,鼻息萦绕在姜早的耳边,沉重、急促。他的声音很沙哑,嘴唇抵在她的耳边,说话时呼吸总是打在她的脖子上,姜早像是陷入一个漩涡,动弹不得,只能缩着脖子就当是反抗。
“那你知道你在我的精神世界是个怎么的人吗?”他淡声。
姜早侧过头,还没问出那句什么样的,整个广场就燥乱起来,原来是到了请花神的时候,花神被香酒和酥香鲜花饼请出来,便前来广场送祝福,盛装出席的蒙面花神带着神水,手指捻着一支桃花枝,见到了人就温柔地往其头上洒水。
结束之后就到了游街,姜早被选中当送花使者,一堆人涌上来为她挂上花串,戴上新的花环。
瞬息之间,何斯屿捡起从桌子上掉落的姜早的简笔画,片刻后,他怕姜早在推搡中摔倒就一直护在她前面,这让花神很生气,他被拉到一边,成了一个敲鼓小生。
他手生地击打着鼓面,目光一直追随着姜早,她像极了一只被人类簇拥的翠鸟公主,雀跃地在人们准备的鲜花之路舞蹈。
此刻,阳光照射在她身边都显得不过如此。
何斯屿心想。
他们挨家挨户的游串扫霉舔福,送花使者有一段固定的台词,对小孩说的是,扫走霉运,为你添上一份无病无灾,一份无忧无虑,一份健康快乐;对成年人是扫走霉运,为你舔上一份不服输的毅力和一份源源不断的财运;对老人是,扫走霉运,为你添上一份无病无灾,一份长命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