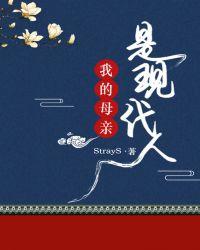极品中文>白月光竟是黑心莲by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何止认识。”周恃宁道,“他是我表弟,两年前他爹在并州做官,升迁回京途中遇上了民乱,一家人就此离散了。原以为凶多吉少了……没成想人好好在你这儿呢。”
裴煦的母亲周韫玉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与周家还有往来。
“得尽快写信告诉小姨夫。”周恃宁自言自语完,又探头去看裴煦,“小姨呢?怎么只你一个人。”
裴煦脸色倏忽之间就变得惨白了,他的头有些疼。
姬元徽想起了他初次见到裴煦时的场景,意识到了什么,皱着眉打断了周恃宁的询问:“你先去前厅坐会儿吧,他身体不舒服,一会儿我去和你说。”
“唉?他的事你说个什么劲儿……”周恃宁话没说完就觑见了姬元徽要杀人的目光,他后知后觉自己应该是问了什么不该问的,缩了缩脖子怂了,“那,那我先过去了哈。”
姬元徽扶裴煦回去,倒了杯茶看着他喝下:“好些了吗?”
“我没事。”裴煦笑笑,“刚刚不知怎的,头有些疼。”
“没事就好。”姬元徽松了口气,“我过去前面看看他还有什么事。”
裴煦点头,姬元徽刚转身又被他扯住了衣角。姬元徽回过头询问:“怎么了,还是不舒服?”
有种莫名的恐惧从心头升腾而起,搅得裴煦心烦意乱,却又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殿下,我有些怕……”
“我在这里,怕什么。”姬元徽安抚道,“我就去说几句话,一会儿就回来。”
裴煦还是有些不安,但又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拖着姬元徽不许他离开,最后还是点了点头,说:“好。”
不知两人谈了些什么,次日再见到裴煦时,周恃宁看向他的眼神变了不少。
他向来不怎么会掩藏情绪,这目光里的怜悯太过明显,看得裴煦一阵恶寒。
裴煦不喜欢别人这样看他,这神色像是在看一只猫,一条狗,唯独不像在看一个活生生的,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来去的人。
姬元徽一边写着往京中裴家寄的信,一边问他,要找到家人了开不开心。
由于裴煦说什么也不肯自己写,姬元徽只当他亲乡情怯,便代笔了。
裴煦心头阵阵翻涌,胃里有些不适,像是想吐。他强压下恶心,安慰自己可能是因为心绪起伏太大才会这样,随后不太自然的点了点头。
得知裴煦没死,还失忆了被姬元徽留在身边,裴家匆匆忙忙派了一行人来接他,生怕他突然想起什么来说出去坏了裴寄的官声。
见接人的来的这么快,姬元徽还当是裴家重视他。
裴煦名正言顺的家人来了,而且似乎很珍视他,姬元徽没有理由硬扣着人不让走。于是他只能在临别时给裴煦乱七八糟塞了一堆东西,叮嘱他好好吃饭睡觉保重身体。
“你先回去,我应该用不了多久也能回京了。”姬元徽这话说出来其实自己心里也没底,但他还是强作镇定笑道,“到时候殿下再带你骑马。”
裴煦抱着他做的那把小弓,哭得眼尾鼻尖都是红的,说:“殿下要给我写信。”
姬元徽手捏紧了,强忍着没给他擦泪,只说会写的,会写的。
后来姬元徽的信一封封寄出去,无一例外全部石沉大海了。
当失望一次次堆叠,猜疑就产生了。
是回了京被富贵迷了眼,不想和他这个被贬斥到边远之地的不受宠皇子来往了吗。
也是,裴家如今也算新贵,大皇子,太子,支持哪个都比支持他来得稳妥。
可万一是裴煦家中不许他胡乱站队所以扣下了信,裴煦自己并不知情呢?
姬元徽心乱如麻。
而另一边,裴煦一直以来的不安应验了。
到了京中,裴家的人并没有像去接他时表现的那样热情。每个人都用冰冷的视线打量他,言语嘲讽,挑衅苛责更是常态。
尤其是他的父亲,望向他的第一眼满是怀疑警惕,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什么烫手山芋,拿着烫手,却又不敢随意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