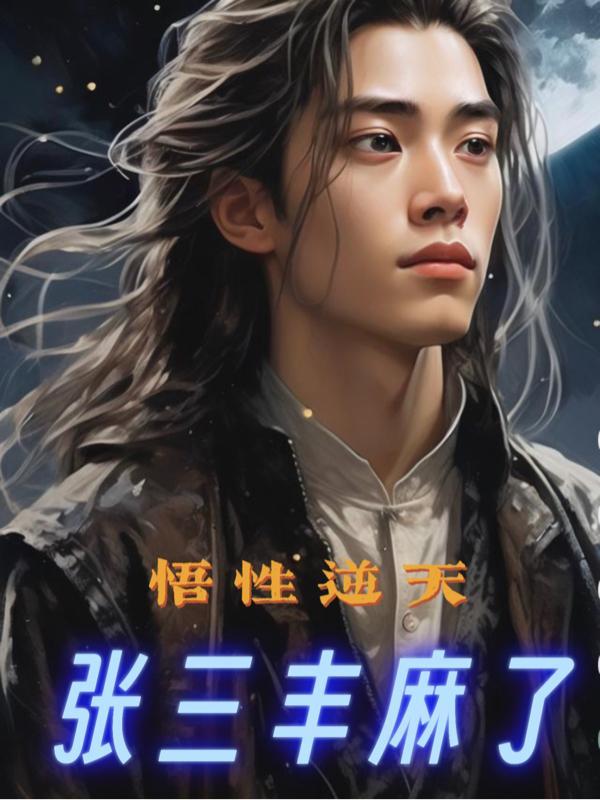极品中文>我zz道 > 第99章 不算突然的想法(第2页)
第99章 不算突然的想法(第2页)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珙壁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这是说天子登基时,设置三公来辅佐他,授予他美玉做的玉玺与四匹马拉的车驾,还不如坐下来对他说这个道理。此处的“此道”即上面所言的“人无完人,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之类的道理。这样,一方面警醒天子自己若犯了错误要知错能改,另一方面也等于劝天子要宽宏待人。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就是“古时候为何如此看重这个道理?不是说:希望犯错的人能够汲取教训而有所收获,改过自新,以后能将功折罪么?因此这道理也受到了天下人的重视。”。此处“有罪以免”显然不是以此为借口逃避所犯的错而造成的罪责,而是因为给了他反省机会而让其知错能改,然后在以后的工作中不再犯错而建立新功,可以将功折罪。
宽宏御下,也算老子三宝之一“慈”的一种表现吧!
第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此章老子劝诫统治者做事要循序渐进,从细小处容易处着手去做好事情。要甘于淡泊,不可躁进。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即:抱无为之心来做事(不急功近利);做不扰民的那些该做的事;要甘于淡泊,乐在其中。此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无为”故“无事”;也因“无为”自然淡泊宁静,故“无味”。又因“无事”故不需费心费力去谋作为;也因“无味”故无生事之心,故少事。绕半天,落到实处即是:抱着“无为”之志,就能甘于“无味”,则可恒持无为之心;则可习以为常“事无事”。故能坚持不懈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去。
“大小多少,抱怨以德。”就是不要计较太多,尽量要以自己的德行去对待别人的埋怨。“抱怨以德”在此处的意思并非“以德报怨”,而是不去管别人的埋怨而坚持自己的德行。在统治者身边,难免有急功近利之人,那些人可能会因为不能尽快地看到成果而埋怨统治者没有雷利风行地施政(也就是前面第五十八章所说的“其政闷闷”的状况)。对于这种情况,圣明的统治者要稳得起,坚持自己的德行,慢慢来实现最后目标。
“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句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要从容易完成的细节做起,夯实基础,循序渐进,才能最终做成难事大事!
“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这是说圣人们从来不会去图谋做大事,但他们就那么踏踏实实从细小做起,却自然而然地就实现了伟大的功绩。此处老子借圣人的行为告诫统治者不可好高骛远,要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实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这是告诫统治者不要骄横口嗨,把什么都看得容易实现了,从而贸然提出过高的政治目标,否则容易失信于人。“轻诺”即轻许诺言。“寡信”,就是信用寡薄,不怎么敷信用。这就好比现在一些国家竞选总统时候选人许下了一大堆诱人的诺言,结果没实现多少。
“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因此,圣人们对待事情总是把难度考虑得很充分,所以最终能顺利克服困难。
总的看来,老子倡导的是踏踏实实、循序渐进地做好事,反对冒进。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此章老子承接上一章继续讲坚持从细小做起并慎始慎终,不妄为固执,大事自然可成。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这句即:安定的局面容易维持,没有显露出失败征兆的事容易图谋;脆弱的东西容易解散,细微的东西容易消散。“泮”,即“散、解”之意。老子在此也提醒统治者,不要忽略小事,要防范于末然。执政之道,须紧记“民无小事”!有些事虽然于大局很不起眼,但对于老百姓个人而言,可能就是天大的事情。执政者知之,不能不理不睬。民众舆情,先起于从个人遭遇角度出去考虑事情,而后渲染传播。闹大了就有损执政者形象。若民间舆论点儿都没有,那就仅两种可能了。一种就是真的仅能同情而已,别无办法。另一种则是相当于对执政者冷眼相望了。毕竟防民如防川般干的人又不是没有。当然,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若这类事积多了,就于大局埋下巨大祸根了。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说:在事情还没有样样的情况下就开始着手去做起,在社会还没有出现乱象时就去着手治理。(此句强调做事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做起)。合着双臂才能抱着的大树,也是从毫端之处生长累积而长成的;九层高台,是从最底下的土垒筑起来的;行千里那么远,还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补充意译下就是:不从基础做起,肆意想当然地妄为,就如同搭建空中楼阁一般,注定要失败的。不顾实情而固执地强行施为,就如同紧握一把沙子一样,越握得紧沙子流失得越凶。圣人从不强求作为,所以没有失败;从不执着硬来,所以不会招致损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说民间人些做事,经常会接近要成功之季而失败了,就是因为不能慎始慎终,临近成功而疏忽大意,造成功亏于溃了。若能慎始慎终,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就是说:圣人追求的是人所不追求的,并不会去稀罕那些难以得到的珍稀货物;圣人学习的也不是常所学的那些谋求利益的本事,而是如何补救众人经常所犯的错(即“复众人之过”,考虑得比一般人周详、深刻。)。他们就是这样来辅佐万物自然而然地成就,但并不敢去妄意扭曲自然地施以作为。
可见,老子始终强调的是要循道(遵循自然)而踏实谨慎地循序渐进来做好事情。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准则、法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此章老子用“以智治国”,反衬“以道治国”,再次强调要“以道治国”,方可“大顺”。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后世对老子这句话的理解一直颇有分歧。
有些人认为老子主张愚民政策,不让老百姓学习,不开启民智。有的人则说老子如此而论是鉴于春秋时社会现实,民风不古,社会上伪诈辈出,因此想拨乱反正,故而提出愚民。有的则说老子希望“愿人与我同愚”。有的则说社会风气是由统治者主导的,老子希望劝说统治者“导民以愚”,从而不自觉地改变政治风气,最终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
反正说法挺多,但都曲解了老子所说之“明”与“愚”。
先,“明”指“明白”,可引伸到“明智”。老子所说的“明”,是“明白”的意思。老子在前面就说过好的施政是要“使民不知”的。与此处所言“非以明民”意思差不多,就是说施政时不是要告诉百姓为什么要这么做。而是要达到让百姓浑然不觉,认为本就该如此。
然后再看老子所说的“愚”。此“愚”并非愚蠢之意,而是朴实的“我自然”的状貌。即“不耍智巧心机、憨厚朴实”之意。故此句应译为:古时善于以道治国的人,不是要老百姓知道为什么要按政令去做,而是使他们浑然不觉地自觉遵从政令,返归于朴实的状态。
通观整部《道德经》,老子一直都是把人民当作社会的根基与本体看待的嘛,一直奉行的都是“人民至上”的原则,怎么可能突然弄出个“愚民政策”来呢?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两句老子就直入主题了。他彻底地否定了“以智治国”,把这种统治者直接定为“国之贼”!
从这出,我们就好理解“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了。因为统治者“以智治国”,处处算计百姓,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故而民间就有了效仿与对策。百姓“多智”,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毕竟“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嘛。
若说民间有少数奸民存在,靠耍奸滑,坑蒙拐骗谋利,也是难免。但在古时这些人都不怎么受百姓待见的,为数不多,远远达不到社会主流,应该不是老子要讨论的对象。除非有些人有靠山,狐假虎威,与上面的沆瀣一气,形成了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否则,他们真入不了老子的法眼。真正入老子法眼的,大家自然就明白了,就是那些“国之贼”!
所以,一切都是“以智治国”搞出来的!而从“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看,老子还是挺简单的。只要不欺诈百姓,老子就觉得是天下之福了。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先解释下,文中“稽式”即“准则、法式”之意。“反”通“返”,“回归”之意。此几句就是说:晓得“以智治国”与“不以智治国”的差别,就晓得了治国的准则(即潜在之意“不可欺民”)。时常遵守治国准则,就是有德了。将德行做到深远,就能带领天下返归自然,这样就能一直顺畅展下去、长治久安了。
很显然,“不以智治国”还并非老子心目中的“以道治国”,但与之接近了。老子心目中的“以道治国”,应该就是那种“大顺”的状况。
老子所言“以智治国”者实在太多,并不只是指那些权谋之士耍花招为国君敛财之辈,而泛指第六十章所言那种“伤人”的统治者。当然,如管仲那种治国能手该怎么看呢?一方面他治国的智巧的确高明。另一方面,他的所有策略无非不过为国君生财敛财而已。齐虽称霸,但齐国人民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益处,齐国也不可能因之长盛不衰下去。或许正因其用心不纯,连孔子也鄙视他“不器”吧?就是说,即使是经济政策,也先应当考虑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展!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此章老子讲谦让不争。
这章挺简单的。多少意译下即是:江海是百川百谷之王,是因为它处于百川之下。所以圣人想得到民众的尊重,必定会言辞谦恭而甘称下位;圣人想列于人民之前,必定会自甘居于民众之后。所以圣人处于民众之上而民众不会觉得负担沉重,处于民众之前人民也不觉得受到了伤害。所以天下之人总乐于推举他作为领袖。圣人就是用他的不与民相争的策略,来达到天下都不能与他相争的。
“不争”是道家提出的重要策略之一。表面上略显怯懦,实则是韬光养晦之策。老子把这点直接整合成对内对外的一致了。对内,统治者不与民争利,必然就能取得民众的拥戴。也正因不争民利,人民就能展得好,国家实力就能潜滋暗长地蓬勃提升,就可以更快地达到民富而国强。对外不逞强争斗,可麻痹敌人,使之放松警惕,为自己获得相对宽松点的时间与空间用于展自我。最终必然还是凭实力说话的嘛!
对于《道德经》此章,有位叫张松如的评说:“这是向统治者献言,颇有点像班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圣人”要想统治人民,就得用言辞对人民表示谦下;要想领导人民,就得把自身放置在人民后面。最后,要做到“处上而民不重,处下而民不害”。难道这不正是当时处于水深火热的广大农业小生产者的迫切愿望吗?事实上,封建统治者当中谁个能做到这一点呢?以不争争,以无为为,这是合乎辨证法的,这也是农业小生产者的经济特点及其阶级利益决定的一种社会思想。当然,他们只能把这种思想作为建议进献给他们所理想中的体“道”的“圣人”。为什么一定会是这样呢?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水和阳光。”
可以看出,张松如先生看得比较深刻,老子为统治者献策都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呐喊。抛开春秋时农民迫切需要国家权力保护的特定历史环境不说,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何时何地人民不需要国家来保护嘛?国家权力本就是社会公权,只是不同时期受不同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而已。民重君轻,以民为本,任何时候都是政权得以长久必须遵守的不二法则!谁不遵守谁就可能把自个给玩完儿!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取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死,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