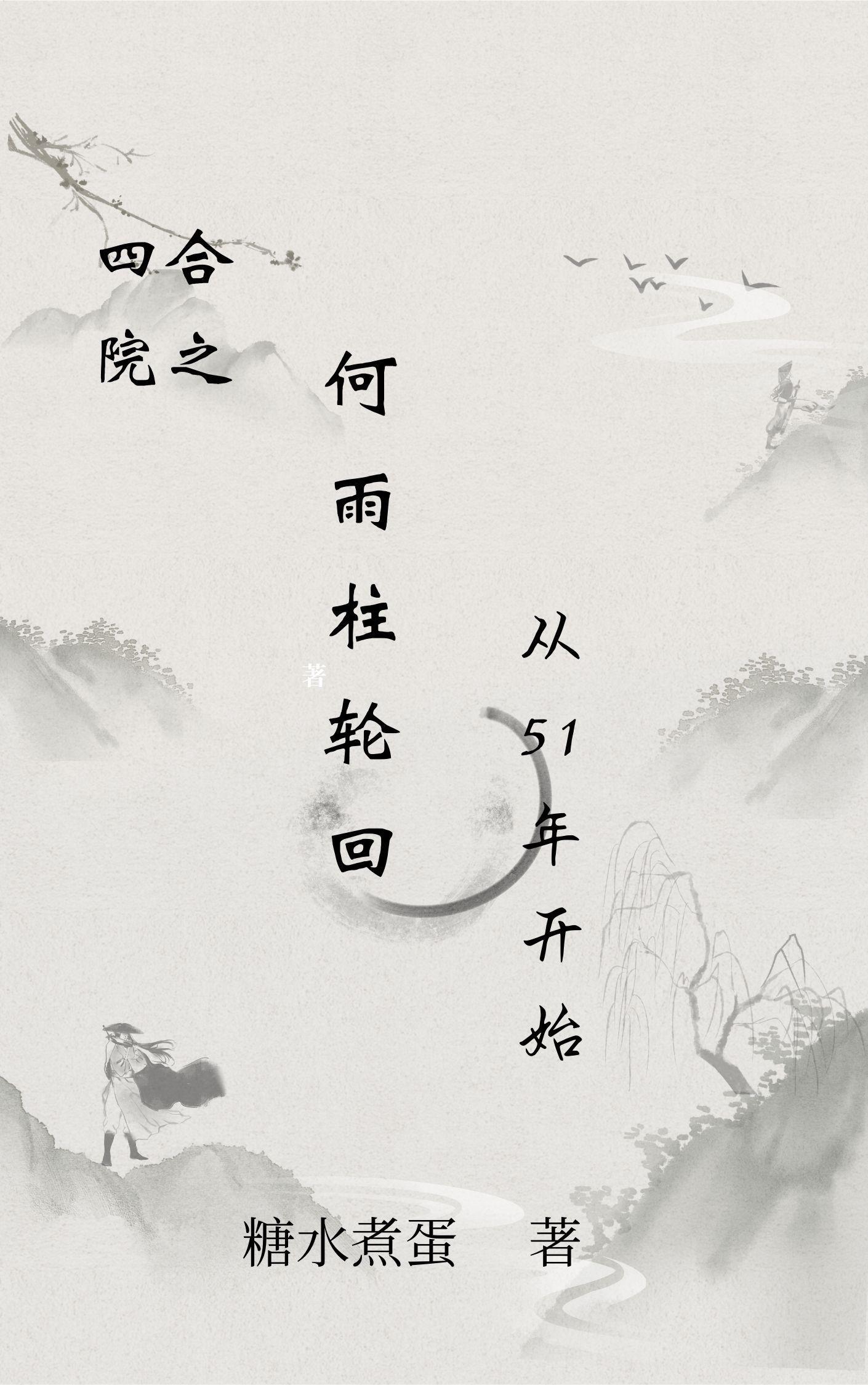极品中文>小夫人又美又甜尽白夜明全文免费阅读 > 第61章(第1页)
第61章(第1页)
他站着不动尽都受了,等她停下来,才将人搂进怀里来温声哄了好半会儿。
临到外头热水送来,便一把打横抱起她,不由分说去了隔间屏风后的浴桶旁,三两下剥光洗净又抱回到了床榻上。
他倾身过来,捧着阮阮的脸重重吻下去,打开她,在她全身都印满他的痕迹,给她柔情的手段,不遗余力地将她方才受的罪一一弥补了回去。
阮阮脑海中是冰火两重天的斗争,她一边神思恍惚地喜欢着他,一边恨恨地想掐死他。
喜欢他的熟悉和契合,也同样讨厌他对她的喜好那么的熟悉和契合。
这感觉像是她在他那里完全没有秘密,从内到外从身到心,什么都是了若指掌。
翌日清晨启程前,驿站的驿丞遣人送了早膳上楼。
霍修换了衣裳拉她坐在桌边,盛上一碗粥递给阮阮,但她晚上没睡好,再瞥一眼那粥,脑子里电光火石间顿时一万种拒绝,遂蹙着眉恹恹的伸手推开些。
“不吃,饱了……”
她说着就要站起身,但刚起来一半,偏又被他拉着手腕扯回到凳子上。
“坐好。”
霍修很有些耐心地看阮阮一眼,兀自端起碗舀起一勺,仔细吹温了喂到她嘴边儿,“近来有些瘦了,不准挑食,多吃点儿饭。”
阮阮闻言下意识低头在身前看一眼,随即昂扬挺了挺胸,理直气壮地质疑他,“胡说,你昨晚上还说长了呢,哪儿瘦了?”
霍修一时语滞,竟不知说她点儿什么好……
辰时末,画春收拾好后早早上三层等在门口,房门打开,便见霍修正牵着阮阮出来。
阮阮带着帷帽有些不情不愿地,隔着薄纱都能教人感受到那嘴肯定噘得老长了。
临至楼梯口,他回身,指尖拨开她面前的薄纱朝里看了眼,屈指在她唇上轻轻揪了下,“让你多吃饭是为你好,行了,笑一个给我看看。”
“哼,明明是为了你自己抱起来更称手,道貌岸然!”阮阮努了努鼻子,敷衍冲他扯了下嘴角,凶得很,“行了吧?”
霍修轻笑着摇了摇头,不再逗她了。
两人一前一后下楼,阮阮有意耽搁了会儿才出驿站,但随行的家丁看了一路,时候久了,眼神儿也逐渐有些狐疑起来。
这日行了一整天未歇,终于在傍晚日落前进了兴城。
阮家的商行同总督府一个在城南一个在城北,这会子便是时候分道扬镳了。
阮阮在城门口与商行前来接应的掌柜碰了面,再抬头看,霍修一行便已纵马拐进了一旁的街道中。
商行掌柜在缘来客栈订好了房间,晚上一番洗漱后,城中已四处挂起了灯笼。
阮阮就靠在窗边的躺椅上,听远处胭脂楼里传来笙歌阵阵,口述一封简短信笺,由画春代笔,送回去给爹娘报平安。
总督府那边儿没有派人来,想来霍修手头事务繁多,一时还抽不开身陪她。
兴城夏季多雨,盛夏的天常时说变就变。
翌日巳时末,朗朗晴空不过片刻便忽地乍起几声惊雷,轰隆隆从头顶上碾过,阵仗颇大。
不多时,果然就有瓢泼的大雨倾泻而下,打在窗沿上劈啪作响。
画春去关窗,背着身说:“小姐今儿要不就先不去商行了吧,林医师先前儿才说了要您歇着,这么大的雨您可不能再淋着,况且账本儿改明儿再看也是一样的。”
阮阮坐在镜子前描眉,说不行,“商行半年的账本儿可不是随随便便能核查完的,我害怕出错,还是慢些、仔细些好。”
她打定了主意,这厢收拾妥帖便直奔着城南商行去了。
一连雷打不动地瞧了好几天账本儿,阮阮都略微有些腰酸背痛起来。
这日睡了个懒觉,正午时分准备出门,才站起身,却听外头有人咚咚在门上敲了两声。
打开来一看,却是霍修派身边的侍卫来接她了。
阮阮站在门上咂咂嘴,商行去不成了,便扭头看画春,“那不如你跑一趟,就说我今儿乏得很不想动,接着前头看过的账本儿拿过来瞧瞧吧。”
她嘱咐后,便随侍卫一道上了软轿。
晃晃悠悠到总督府门前,挑开帘子抬头看,气势一如大半年前她初次上门时威严,往里头去,纵深的宅子飞檐翘角,四处都是凌厉肃穆的线条。
她看多了霍府私宅中的小桥流水、曲折游廊,再进这里,才觉着霍修骨子里原也是个喜欢诗情画意的人。
府中侍从径直带阮阮去了个名叫“雅庭”的小院,霍修并不在,听说是还在会客,要她在此稍等。
等待的时候,画春先回来交差了,紧着心教两个小厮抬着一箱子账册进来放在了长案旁,歇口气,还带来了阮老爷的一封回信。
阮阮先打开信,但才看了个来回,面上却陡然暗淡下来。
画春在一旁整理账册,余光瞥见了,忙问她:“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吗?”
阮阮摇了摇头,抬手将信递给画春,颓然说:“你瞧吧,我爹光是听说我来兴城这一路恰好与霍修同行,就担心非常,在信中千叮万嘱要我离他远一点了。”
画春闻言低头去瞧,信中阮老爷所言,霍家高门权贵,阮氏小小的商户惹不起,要阮阮寻常少在他跟前走动,奉行惹不起但躲得起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