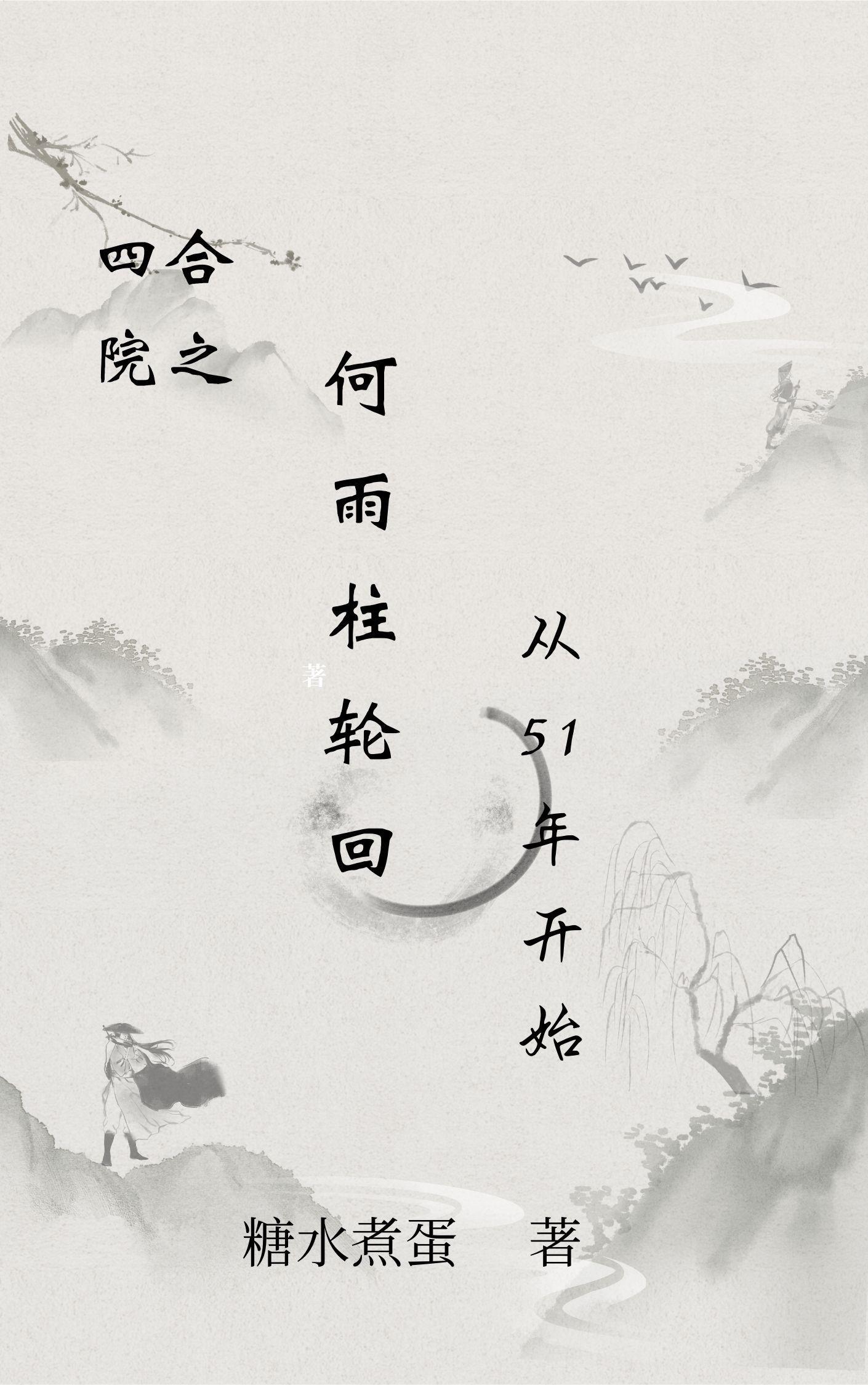极品中文>锦衣卫三兄弟电影叫什么 > 第一章 腰牌(第1页)
第一章 腰牌(第1页)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不信命,觉得人定胜天,便借着自在之名投身江湖之中。
在江湖中见了山就想攀,去看山后面是什么,哪里知道,山后面还是山。
有朝一日头破血流的醒来,无非两句诗,十个字:到头一场梦,万境皆是空。
这道理就算早些明白,还是会一无反顾的猛身扎进去,妄想将这世搅他个天昏地暗,浪翻云涌。
明朝天启年间。
顺天府,崇文门,清晨。
二月红杏闹枝头,可这崇文门闹市中的百姓无一人有闲情去赏,皆是身穿麻棉厚衣,低头前行,背上压着的不是沉重货资粮食,而是这明朝末期的苛捐杂税和阶级压迫。
闹市中一挂着“苔花居”幡子的鲜亮酒肆在麻灰色的集市中格外显眼,这酒肆只一楼,有前堂后院,后院是店家自住,也建了酿酒的屋子,前堂招待酒客旅人,摆着格格不入的上好黄花梨酒桌。当中坐着一位细眼卷发少年,清寒的天气却身着的桃红丝绸争春单衣,他虽是这酒肆的主人,却无意招呼酒水生意,只是端着一碗酒边喝边在上好的宣纸上疾书。
“陈二!”随声窜入一人,一晃就坐到了卷发少年身边。
陈二还未反应过来,肩上又被重重拍了一下,碗里的酒洒去大半,耳里听到“来壶酒!”
“一壶?就你那二两的量!”陈二拍掉衣裳沾的酒,看向窜入的少年又问,“这么快就回来,连试监都没进吧?”
这少年随意扎着头发,浓眉大眼,老虎鼻配上也算有棱角的脸,唯一让人有印象的是右眼角下一颗红痣,身上藏青单衣用黑色束衣带一扎,薄底快靴一踏,白净的皮肤加上这打扮,看着干净利落。他“哈哈哈”大笑:“我老爹非要我考这鸟会试,我才不考,临进号舍我就溜走了。”
陈二抿嘴一笑明知故问:“那明日你老爹安排的锦衣卫选拔?”
少年拿起伙计端来的酒壶,直接猛喝两口后“啪”地将酒壶一放,摆手摇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我何三志不在仕途,不愿食君俸禄!”少年声大气足,全然不顾周围酒客眼光。这两句,要是被东厂番子或锦衣卫听到,添油加醋一说,可算得上是邪言逆语,弄不好要进诏狱。
“那你要做甚?学了文武艺,总不可能和我一样每日守着这‘苔花居’吧?”陈二没有因为少年的话感到诧异。
“我哪有你这富家子弟的闲情,我只想涉川渡水,游览山河!”何三又是两三口喝光壶里的酒,拿着酒壶晃了晃:“我说陈二,你这哪进来的酒?”
陈二放下手中乌翅木雕狼毫,凑到何三耳边神秘说道:“好喝吧?小爷我自己用苔花酿的。我还发现,玉麦用来酿酒,酒色清,酒香远而不散。加了这两种配料,才有你喝的这上等佳酿!这可是‘苔花居’今后发财的倚仗。”
“这些我不懂,我只管喝就行,再来一壶。”何三把喝空的酒壶递给陈二憨笑。
陈二压下酒壶:“那不行,你现在要是喝多了,待会岳俊忠,陆沐春,陆厚德,丁铭,王象升他们来了,你又要逃酒。”陈二把二人共同好友的名字一一念出,像是在提醒何三,他们几人好久没有一同喝酒言欢了。
陈二说到“丁铭”时,何三愣了一下,等陈二话音一落,他起身往后院走去,几个弹指便打了一个行囊提着一把四尺黑鞘黑把刀出了帘布。
“才喝了一壶就走?”陈二起身拦住何三,面露疑惑,“我还想让你看看我刚写的商策呢!还是说,你又想要逃酒?”
何三从腰后掏出酒葫芦递给陈二,苦笑:“我哪里要逃,你先把这酒葫芦灌满了我再告诉你。”
陈二与何三打小认识,一同入塾念书,一看何三的神色就知他没骗自己,肯定是遇上了事,起身到柜台后打好酒,走到何三身旁把酒葫芦曲臂护住又问:“莫不是你与王象升又有争吵?”
“没有,自从王象升去年末进了神机营我便再也没见过他,这次来城内我还想和他喝酒聊天咧。只是你刚才说到丁铭,我才想到,来时我老爹要我去找丁伯,这事要紧,我先去办妥了再来喝酒。”何三紧了紧行囊,“我先办完事,回来再看你写的商策。”说罢,抢过陈二手中酒葫芦,快步出了“苔花居”,人影没了才听到他大声说道,“我办完了事就回来,很快!”
陈二看着门外,呆了一会,苦笑着喃喃自语:“恐怕这酒你又要逃了。”
何三出了“苔花居”直奔东安门外十王府方向。他一路快走心中琢磨:“父亲从未给人送礼,这次却拿出一个锦盒交给我,让我务必上丁伯家当面送予他,不能出半点差池。我问盒中是什么物件,为何送礼时,他老人家只是看着我沉默不说,想必和我有关了。只是究竟什么事,值得父亲如此?”
东安门外,一条没有高墙深院、王府官宅的巷子。这巷子夹在金銮殿与十王府中间,在这个位置购置宅院,既能快速到达皇宫,也能在闲暇时拜访高官大臣,这些住户当中,中阶官吏居多,富商也有几户。
何三来到挂着“丁宅”木匾的乌头门前。先是闻了闻身上是否还有酒气,才上前敲响门环,开门的是一绿衣丫鬟,模样倒是乖巧,她站在门中,看到寻常穿着还配着刀的何三,也不怯声,清脆问道:“你甚么事?”这语气却有些傲慢。
何三心里轻笑:“这丫鬟当真是门缝看人。”也不做礼:“你和丁伯父说,何永兴之子拜访。”语气也不客气。
绿衣丫鬟听出何三和家主不是一般关系,连忙关了门转身入宅,不一会,宅门打开,走出一名脸颊消瘦,鹰鼻薄唇的中年男子,他见了何三面露微笑拍了拍何三肩膀:“好久不见。家父刚做完朝课,你先进来等会。”
丁枭是丁铭的大哥,原先也是锦衣卫一员,在天启元年“移宫案”期间,王安命他护卫天启帝朱由校有功,从锦衣卫升作京卫指挥佥事,今日恰好下了夜间勤务在家休整。
“劳烦丁枭大哥了。”何三拱手做礼随着丁枭进了宅门。
丁宅是三进的院子,院内也没种树,左右两侧分别摆放着兵器架子和百斤石锁,唯一的装饰是西北角筑的一个一丈鱼池,池内放了一座青苔假山,几尾彩色锦鲤游曳其中,也有些意境。
丁枭直径带着何三来到书房,显然,何三所来何事,已被知晓,更有可能,这事就是丁枭之父——丁冷山安排的。
“你坐着等一会。”丁枭说完,转身带上房门出了书房。
何三哪里坐得下,只是站在房中,暗自琢磨。
不知过了多久,房门打开,走进一位微胖的半百男子,宽口阔脸,黑须满腮,身着御赐飞鱼服,不苟言笑,双眼射光。
何三听到动静,连忙转身拜礼:“丁伯父。”
丁冷山“嗯”了一声,先是关了房门,才伸出手托起何三。
丁冷山走到桌后坐下:“思远,东西带来了吗?”声音浑厚低沉。
何三不紧不慢地解下行囊,取出锦盒,递上前去。
丁冷山拿过锦盒打开来,盒中先是透出一丝寒气,再显一阵白光,白光散了才看清,盒中装的是一具飞禽骨架,这骨架长不过二尺,单看这飞禽钩爪锯喙,隐隐透出杀气,加之这骨架全部玉化后冷冽非凡,肯定不是俗物。丁冷山看到骨架完好无损,盖上锦盒:“我与你父亲原先一同在南镇抚司共事,平时甚好。你父亲原本可以升做千户,可他为人正直,太过秉公办事,得罪了不少人,被调到北司办事,过了这么多年还是百户。这次送来这海东青玉骨,却不是为了自己升做千户,而是另有一事。”丁冷山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看着何三。
何三心里只猜到这事与自己有关,用躬下拜礼的身形询问具体是什么事。
丁冷山拿出一块铁质腰牌放在桌面,“思远,你拿起来看看。”
何三拿起腰牌一看,额头瞬时冒出细汗,这牌子上除了铸着自己的名字外,还铸有“锦衣卫校尉”五个大字!
丁冷山上身后倾,靠着木椅,看着惊愕的何三,淡淡说道:“你父亲料定你不会参与锦衣卫校尉选拔,便为你求取锦衣卫职务。这锦衣卫小旗以上职务需圣上亲笔批文方可授职,百户以上授职,需面见圣上,还可受御赐飞鱼服、绣春刀。你这校尉一职无需这些繁琐,我与指挥使骆大人打声招呼便可。现腰牌在手,你已是锦衣卫校尉,校尉不分南北司,好好干活便是,切莫负了你父亲对你的厚望。”丁冷山几句话,一是说明收礼为了何事,二是说明这事办得已到头,入锦衣卫当个不入流的校尉,看似简单地说几句就能定下,却也那么不是容易的。
“这……”何三呆住了,原以为只要过了明日,就可以不入仕途,自己逍遥快活,可谁知道,就算自己不参加选拔,还是被迫卷入了这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汹涌的“江海”之中,而这来自父亲的厚重期望,还让自己无法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