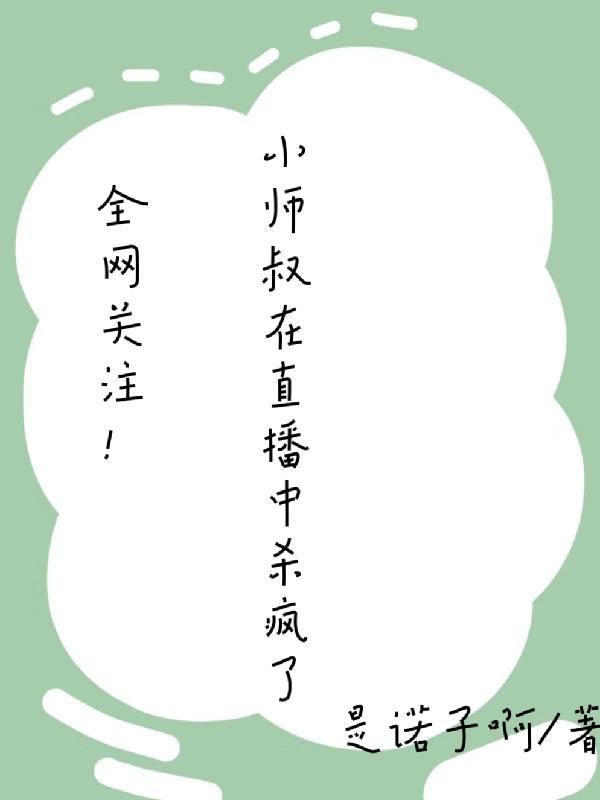极品中文>越冬by咚咚锵 > 第28頁(第1页)
第28頁(第1页)
他刻意保持距離,隨手打開電視,姿態懶懶:「你怎麼又回來了?」
「害怕你失血過多。」
屁,就是心裡堵得慌,不想回家,正好他離得最近。
關越嗤笑一下:「怎麼找到我家的?」
「我看見你進了這個樓棟,恰好那個時間段就你這一戶的燈亮了,我就上來碰碰運氣。」
「呵,」關越一手撐著腦袋,無聊地跳台,「你在那玻璃缸里游真是屈才了。」
程諾聽出來他是在笑話她,也無謂:「手,我給你包一下。」
她還沒忘正事。
關越沒有猶疑把受傷的那隻手伸過來,傷口有點泛白,剛才被水泡的。
他頭髮還濕漉漉的,沒有徹底干。
程諾從藥袋子裡掏出消毒液,用棉簽沾了點,塗在關越的傷口上,他手微微動了下,兩人之間距離有點遠,扯著有點吃力,程諾往他跟前湊了湊,一股雨後露水的清鑽進鼻腔。
塗完消毒液,用紗布纏了幾圈,固定好,她鬆開關越的手。
空氣有點灼燙,程諾搓了搓大腿根。小南城巷是個舊的居民區,樓層都不高,從窗外看出去,月色濃稠,風吹著樹葉沙沙作響。
關越把電視頻道調在一個爆笑的綜藝節目上,程諾腦袋裡像裝了個屏障,除了他淡淡的呼吸聲,其他的都被自動過濾了。
那種灼燙也越來越濃重,他也不趕她,兩人就干坐著氣氛有點怪。
還是程諾先開口,問:「有沒有煙?」
關越這才把視線轉到她身上,漆黑的眸光看不出神色,半晌輕飄飄吐出一個字:「有。」
他從小茶几下面掏出一個煙盒遞給程諾,提醒:「只有男士煙。」
「可以。」
程諾抽了一根出來,咬在嘴邊,手塞兜里摸了摸,沒帶打火機。關越看見她的窘迫,又從同一個位置拿出打火機放她旁邊。
火星碰著菸草,煙霧繚繞。關越眯了眯眼,有點不悅。
程諾以為他是討厭自己的煙味,起身趴到陽台邊去抽了。他家的陽台上擺了一些花花綠綠的植物,長得都一般,看得出來關越不是個會打理的人。
還有好幾個花盆裡放了彩色的石頭,小孩子的傑作。
雖然見過幾次,但還是難以想像他照顧小孩的畫面,程諾望著頭頂那抹圓月,悵然若失。
寶貝,她突然想到這個詞。
她為什麼不能被當成寶貝?
所以有時候明知道周成郁的品性,卻還是想著再走走看,最後弄了自己一身泥濘。
現在,那段情被斬斷,她忽然就像沒有了雷達的探測儀,摸不准方向。
生活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重心,有點搖擺。
以前她很堅定,目標就是賺錢、攢錢然後帶著母親去瀛州和周成郁一起生活。突然這樣的目標被生生截斷,她饒是已有心裡準備,還是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