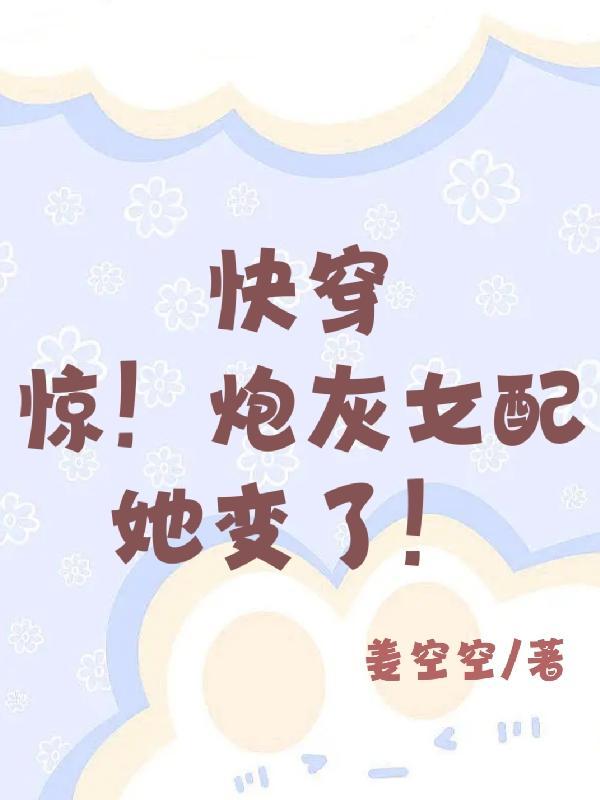极品中文>女王赐予他的花[女a男o > 第36章(第1页)
第36章(第1页)
这几年的死遁,就是颜休计划了多年,为自己谋求的一个置死地而后生机会。
时劼算出她有帝王相,也算出她不会一帆风顺,势必会有一次大的挫折。
现在命中的坎已经度过,如何顺风而上回到原位是另一件事。
这些都是洛弗因所不知道的,时劼拿起另一块毛巾,无奈地替她擦干还在淌着水珠的发尾,他吩咐少年离开,水边就剩下他俩,时劼坐到了她旁边。
“你家oga在门外找你,等了一会儿之后,被我拦回去了。”时劼保养很好的手柔柔按住颜休还在翻动文件的手,强迫她正视自己。
岁月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一如颜休十岁那年见到他的样子,她在心里啐了一口老妖精,这些天为了让她恢复记忆,吃药、扎针、检查各种手段用了个遍,颜休怀疑,但凡有人说有用,他连电击都能用到自己身上。
最主要的是,他隔绝了她与外界的联系,当她想起自己和洛弗因的关系,想要回去找他的时候被软禁不让离开,明明她是女王,在这里一点自由的权力都没有。
看颜休表情愈发冷漠,时劼笑着问她,“生气了?心疼了?”
颜休抽回自己的手,元老院在颜休那两年的打压下,势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而最重要的枢密院,相比于洛弗因更听从时劼的话,她冷笑道,“岂敢,现在这个国家实际上是老师做主,你可有把我这个王放在眼里。”
时劼没有恼怒,反而一幅在思考什么的样子,其实,有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他的手拂过颜休脸颊侧的碎发,眼神里是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深情。
“我可以让你见他。”他在颜休的侧头躲闪下收回了手,“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以及,我有条件。”
听他说完,颜休直直地盯着他几秒,出乎时劼意料的是,颜休居然噗嗤一声笑了。
她似乎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一般,这种态度让时劼暗自拱起一股火,微蹙起眉头。
笑过之后,颜休的目光突然变得冰冷,即使是一手栽培出她的时劼都感觉有些畏惧,“老师,您似乎产生了一些错觉。”
“不过在你这里待了几日,就认为已经能够控制我?”颜休挑起一缕他的头发,像在欣赏,也像在把玩,如同上好的绸缎一般,滑顺难捉得逃离指尖。
她收回手,语气严肃面上又带着讥讽的三分笑意,“说您权力大,并不代表您真的可以踏在我头上肆意妄为,别忘了,我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
见颜休较真起来,就知道她生气了,每次都是这样,只要碰到洛弗因的事情,这个原本“听话”的“好孩子”就会露出藏好的锋利锐爪,再靠近就会毫不留情抓得血肉模糊。
所以他才反对颜休娶洛弗因,明明有更好的人选,更稳重明理的,更懂事温顺的,而不是每次遇到洛弗因那个愣头青,颜休就也跟着意气用事起来。
不过这些时劼都没有说出口,颜休说的也是事实,在她私人的事上,时劼的确是逾越了。
“是,陛下。”时劼垂下眼,叠手行了个标准的臣子对君主的礼。“臣不敢忘。”
“嗯。”颜休见他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即使被她说到这个地步都没有太大反应,能屈能伸得无趣过头,突然好奇到底怎样才能打破他这张固若金汤的假面。
她托起腮,眯着眼看他,“说来,认识老师这么多年,您好像从来没有生气过。”
不同于洛弗因的喜怒于色,时劼永远是一幅优雅、凡事皆在掌握之中的感觉。
时劼听她这种语气,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颜休坐起身子突然靠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颜休在两人鼻尖还有一拳距离的时候突然停下,她弯起唇笑了下,抬手抵住时劼的肩膀把他推到了水池中。
冰冷的池水灌入衣物和口鼻,时劼的长发和衣袍宛如水中盛放的墨莲,他毫无防备猛吐出几个气泡,挣扎着从水中站起来的时候,水珠顺着脸颊滚落,他把湿发拢到脑后,露出一张秾艳带有森森鬼气的脸,面色更加苍白,眼神像是在骂人,抬手掩嘴咳嗽了几下,饱满的嘴唇鲜红泛着水光,止不住地颤抖。
“你!……咳咳!咳!”他所有的话都被呛的水憋了回去,时劼眉毛立起,这的确是颜休第一次见他反应如此之大。
颜休蹲下,与他的视线相持平,面上带着礼仪满分恰到好处的笑容,“老师,这样看您倒是多了不少的人情味。”
“这回儿有没有觉得你的衣服很碍事?”颜休从小就想吐槽,每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装神弄鬼故弄玄虚。
时劼奢华的长袍此时吸满了水,宛如沉重的金属盔甲,贴在身上十分冰冷难受,感觉就像是拉着他往下坠。
他愤怒地攥起手,咬住自己的下唇留下一排牙印,“你可真是有长进。”
颜休本身性格其实是带着些王室贵族的乖张恶劣的,只不过这些年为了扮演好女王这个角色掩饰了起来,这回死里逃生做事反而不会像以前瞻前顾后,她也向他刚刚一样,恭敬地回了个礼,“老师教导得好。”
“主人!”听到落水声响的少年跑了过来,见时劼立在水池中央手足无措地想要去帮忙,对着罪魁祸首颜休大喊,“你在这傻站着干嘛,还不过来帮忙?”
颜休耸了下肩,弯下身对时劼伸出手,弯着眉眼,“老师,日落水凉,待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