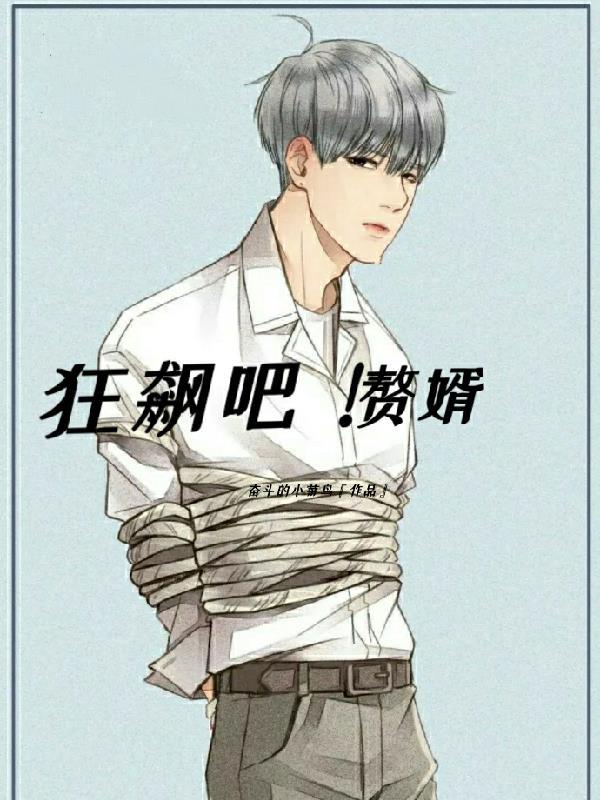极品中文>春潮泛滥的读后感 > 第46章(第1页)
第46章(第1页)
浴袍松软,厚厚一堆,韩泽玉却能精准抓住白耀的手。
下一刻玻璃门乱响,人被生拉进房,紧接着水流直直砸下,就浇在白耀头顶。
故意开到最大,只需几秒里外全透。
白耀头发毡子一样覆下来,冲得睁不开眼,就这样还不满意,韩泽玉不许对方乱动,抱着,让白耀始终处于喷淋中心。
穿衣服挨浇可不像光身洗澡那么舒服惬意,西装如铠甲,与衬衣一道牢牢粘住皮肉,想也知道有多难受。
“抱歉,脚滑了。”
像是玩够,松开白耀,韩泽玉抹去脸上的水。
喷头仁慈地关上,流速过于生猛,脚底一层水,四面乌泱泱雨帘似的还在淌,足见方才这个小小浴房下过多么大一场弥天暴雨。
不痛不痒的道歉,听不出一点诚意。
韩泽玉看都没看白耀,拉门就要走掉,却没能成功。
门上抵来一只手,白耀封锁去路。
这人头发湿透,随意向脑后一捋,白耀五官线条偏硬,无形间加深了身上冷冽的气质,不太好惹的样子。
“你的雏鸟情节就不能收敛一点?”
这就是针对苏姨事件的一次‘报复行动’,针鼻都比韩泽玉的心眼大。
“来打我啊。”
“……”
白耀最终抬臂,拧着眉看对方擦身挤过,出了浴房。
出来,就是桌上放着的茶点。
苏姨段位实在是高,晾了这么久,羹都还未泻,只是在碗沿存有一层浅浅汤水。
韩泽玉味觉还在时极爱这种带汤的,经常拿着扁勺,端端正正坐桌边,一面压水吸溜,一面等着变出更多甜汤来。
可惜,现在只能眼观,用视觉上的甜来满足自己。
韩泽玉收紧浴袍,在指间打着结扣,看着这碗淡淡桃色的羹,被炼乳染成不均匀的粉白,扁勺就静静躺在碗旁,苏姨记得他爱这样吃。
勺伸进搅了一搅,他将半碗倒入嘴中。
没味道,吞下再多也一样。
像是跟什么较劲,韩泽玉大力咀嚼,又吮又嘬,两腮深深陷入。
直到背后传来一声“韩泽玉”,才将他从偏执的行为中解救。
一瞬,说不出哪里累,就全身心往下坠,好似这一身筋骨再支撑不住,不过,下一刻他就全然复原。
他听到白耀问了这么一句:
“吃不出味道来啊?”
片刻极静,只有墙上表针滴答行走的声音,韩泽玉背着身,有些失笑:“什么?”
“甜的还是咸的?”
“?”韩泽玉回过身,不明所以。
对方语气平平,又问了遍。
样子坦然得韩泽玉都要怀疑自己的听觉,桃花羹怎么可能咸,苏姨拿手也是甜品。
白耀第三次发问,仍旧重复这个问题。
事情开始变得有些蹊跷。
这个人不会随口一说,话少则句句为实,白耀从不浪费口舌开玩笑,韩泽玉盯着他看,拿起炼乳鼻下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