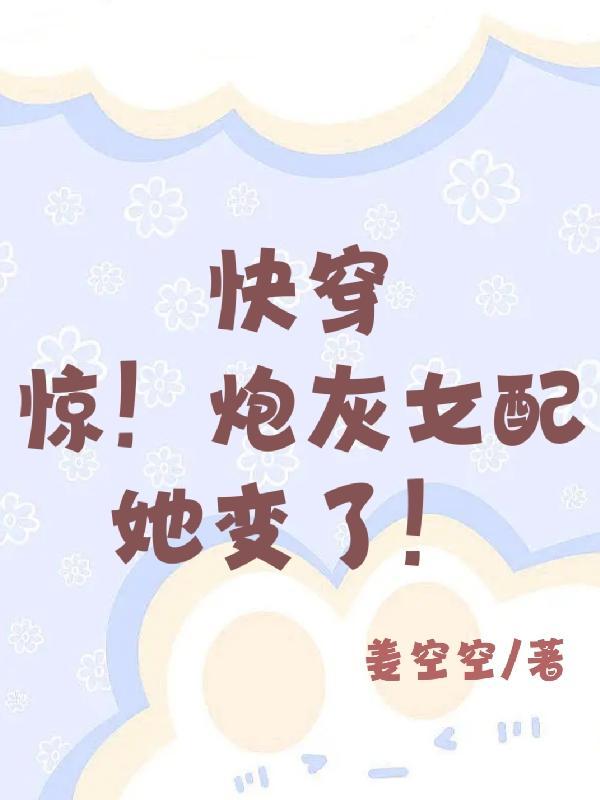极品中文>报恩是什么 > 第9章(第1页)
第9章(第1页)
“唔。”他微微沉默了一下,想起方才母亲的叮嘱,也想起先前安智熙跟梅承嗣说的话。连承嗣都看不过他的冷淡,他是真的太冷淡了吧?虽说一开始是为了互惠互利而结的姻缘,但终究是要跟自己过上一辈子的人,或许他是亏待了她。
“给我吧。”他说。
宝儿愣了一下,不解地望着他。
“把药给我。”
“是。”宝儿这才反应过来,赶忙将药盅交给他,可脸上还是困惑。
拿过药盅,他走进屋里,内室传来三个女人说话的声音,似乎是房嬷嬷在跟安智熙说着宁和号走水的事情。
他穿过一面帘,再绕过绣屏,只见房嬷嬷跟春月已帮安智熙擦好身子并更衣,此时春月正在给她梳理头发。
“爷……”房嬷嬷见他进来,先退到一旁,大概是看见他手上端着药盅,立刻以眼神示意春月,要她赶紧完事起身。
春月再大略地梳了几下,便起身往房嬷嬷身边一站。
他驱前,自若地往床沿一坐,两只眼睛看着手上的药盅,淡淡地说道:“你们去忙吧,这儿暂时不需要你们。”
“是。”房嬷嬷跟春月答应一声,一前一后地走了出去。
看着这一切,安智熙有点愣住。她没说也没问,只是两颗眼珠子定定地看着他,直到他用调羹舀起一匙药汤。
“你……”她微微地皱起眉头,“这是做什么?”
“看不出来吗?”他说着的时候,已经把调羹凑到她嘴边。
她本能地往后缩了一下,皱了皱眉头。“你突然这样,我惶恐。”她说。
“什……”他想对她好,她惶什么恐?
“为什么突然对我好?”她问。“你以前不是这样。”
“不好吗?”他浓眉一皱,“你我夫妻一场,难道不希望我待你好?”
他这么说也没错,要是安智熙还活着,一定会被他突如其来的关怀体贴感动到痛哭流涕,可对她来说,这种关怀体贴的举动是种压力。
她来到这儿是有任务在身,并没想过会过上另一种人生。再说,若她还是个待字闺中的闺女那还好办,可偏偏安智熙已是人妇,她才穿越而来就得照单全收,还得负起传宗接代的重责大任……喔不,她真的办不到。
不管他是什么潘安在世,她都没办法跟一个如此生分的男人过上夫妻生活。更何况,他先前明明因着安智熙的娘家跟她的出身对她十分防备及淡漠,就算在安智熙怀上孩子时,他也只比往日多关心几句,压根儿不上心,为何现在会……是谁跟他说了什么?还是他良心发现?
对了,宁和号走水该不是跟海上流寇有什么关联吧?那么他突然关心她,是因为有求于安家吗?
不知怎地,她忽地为安智熙抱起不平。
“我嫁来两年,你现在才想着待我好?”她直视着他,神情冷肃。
瞧着她那副“我不稀罕”的表情,梅意嗣心头一震。看来,她是不领情。可她不是跟承嗣说看着看着,也就喜欢了他?若她心里是喜欢他的,那么应该乐见他如今想待她好的改变呀!莫非,她那句话是诓承嗣的?
“看来,你是不乐意我待你好?”他将调羹搁回药盅里,眼神如冰似的冷冽。
“两年来,我们顶多算是相安无事的夫妻,却不是相亲相爱的眷侣。”她不像原主或是这时代的女子,碍着礼教传统便将满副心事及委屈全塞在心里,她有什么就要说什么,免得憋出一身的病。
“我们两家是因着什么而成的姻亲,不用我说,你心里也明白。”她直视着他的眼睛,尽管他的脸色已十分难看。
“很多事很多话,我不想再搁在心里,今天就一次把它说分明吧。”她续道:“你对我安家多所提防警戒,从来都不交心,你我虽有夫妻名实,却也是为了维持表面上的和平,就跟你的名字一样——没、意、思。”
她真佩服自己,居然信手捻来随口就说出这相关语。
我现在不喜欢你了(2)
听见她这番话,梅意嗣登时瞪大了眼睛,惊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虽然她是个性情纵放不羁的江湖女子,可过往两年双方都有着不道破的默契,谁也没把心里话说出口。
可今天她却……他该感到懊恼,甚至该有点生气,但不知怎地,他竟没有。
梅意嗣直视着她也正直视着自己的双眼,她那一双过往看起来机灵狡黠的黑眸,如今竟澄净通透。
“方才母亲对我说,你这一劫伤的不只是身子,还有心。”他唇角勾起一抹笑意,“但现在看来,你还伤脑了。”
他这意思是说她疯了?对,她突然跟他说这些话,是够让他惊吓得掉下巴。
“经历此劫,我只是突然想通了、明白了很多事。”她直视着他的眼睛,率真无畏,“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我这次难产险些连命都没了……躺着这几天,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不想再隐忍委屈。”
听着,他竟忍俊不住地嗤笑一记,“隐忍?委屈?”他从鼻子里哼出气息,不以为然,“梅家纵你由你,你何时隐忍?何时委屈了?”
“想说不能说,便是隐忍。想说不敢说,便是委屈。”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我出嫁前可也是阿爹兄长捧在掌心上的一颗明珠,原也想着能被宠爱怜惜,可你对我只有相敬如宾,从没半点真心实意,试问,我不委屈吗?”
他不温不火,两只如炽的眸子直射向她,“那你对我可有半点真心实意?”
“有。”她毫不犹豫的回答了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