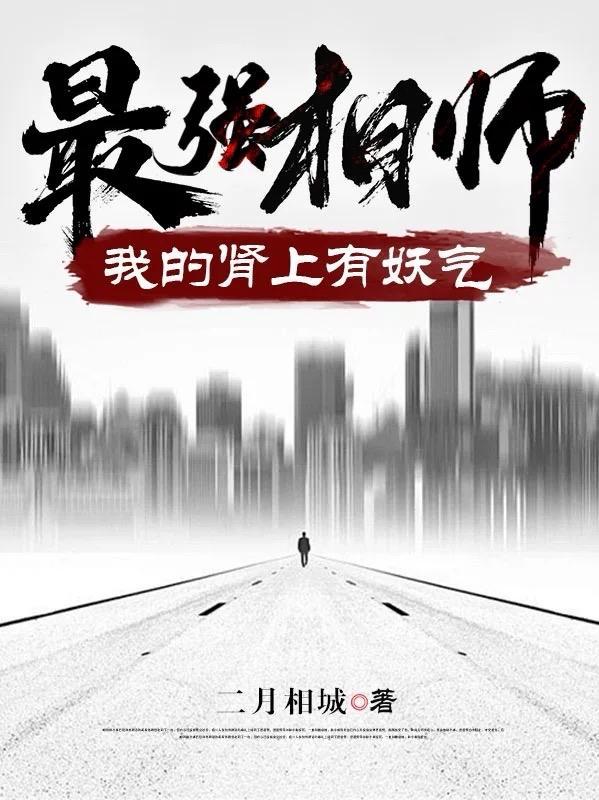极品中文>装B的B作者黑三喵 > 第14章(第1页)
第14章(第1页)
“其实我们可以先试试,傅匀,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治疗……”
傅匀说:“治不好的。韩音,你不会是例外。”
服务员此时才拿着点菜单过来,而韩音拿着自己的东西毫不留恋地走了,随后服务员就一脸无措地看着我们。傅匀并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无奈之下我挥了挥手让他先离开。
从卡座这里到饭点门口不短的一段距离,韩音一次都没有回头的迹象,走之前,他有些生气的看了我一眼,我隐约记得在我刚认识傅匀不久时,那位可爱的、大冬天穿着裙子的omega女士也对我露出过相似的表情。
后者也许是因为傅匀撵走她感到不开心,前者极大可能是因为觉得被我看到了狼狈的一面而悲愤。
我很无奈。要知道事情的走向从来不是我能控制的。
傅匀依旧保持那个姿势坐在座位上没有动,神色也看不清。正当我感叹在这种情况下傅匀也能睡着时他突然出声:“我母亲去世后,这样的相亲我每年会遇到十次以上。”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想了想我说:“那你这算有经验,我没相亲过,以为今天能有初体验,结果被你堵在这里出都出不去。”
“你在怪我吗乔浅?”
“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出这句话,但这也让我确定了他今天不太正常。应该来说,从回到这个城市之后,傅匀周身的气压一直都很低。只是他刻意隐藏,我刻意忽视不去细究。
“怪你不告诉我你表弟一家也回来了,怪你不告诉我你其实有一个名存实亡的未婚夫,还是怪你把我扯进旋涡中央?”
傅匀没有说话,应该是默认了我的说法。
我叹了口气,觉得老天爷在创造我的时候肯定把运气瓶打翻了,于是导致我从小到大一到关键时刻就会遇到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事情。
“傅总,说实话,我们都是成年人,有些事情自己心里清楚就好,说得太清看得太通透是一种类似自残的行为。”我顿了顿,朝窗外偏头,“来的时候看到这附近有小吃街,去逛逛吗?”
。
我出社会之后,最开始的两三年过得很艰难。
除了没钱没权之外,我大学里一个同学还老针对我,就怕我什么时候回去抖出一切,即便拿不到保研名额也能顺势削他一层皮。有一段时间我一边兼职一边找工作的时候总感觉有人跟着我,后来才知道那是他请的私家侦探。
我和谁说话,说了什么,去了哪里,去干什么,所有东西都事无巨细地被整理成了一份很长的报告。
第一次看到那份报告时我很震惊,可能是因为连我自己也没意识到其实我不喜欢吃香菜,我说话时会无意识带上犹豫的语气词等。
被人惦记是一件很新奇的体验,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每天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工作中的忙碌和不顺心都快将我吞噬,被人跟踪什么的,对于我而言并不能排上号。
而那个私家侦探被我打了一顿之后再也没有出现在我周围。
再次见到黎小梨是我不得不回一趟家的时候。
他当时和梁呈正处于热恋期,看到我的时候很高兴,一不小心就忽略了男朋友的感受。
黎小梨说我变了。他说我曾经那么意气风一个人,现在就好像一潭死水。他一直追问我生了什么,我也只好打着哈哈跟他说一切安好,甚至遇到了大学同学,他给我介绍了一份文字工作。
当时还不太会伪装。
他还想多问些什么,我实在记不清我是怎么回答的了,只觉得世界很烦。
作者有话说:
有一件乔浅永远不会说的事
他暂停了一切工作,打算等手里的存款快花完的时候买一张去国外的票。
他有想过终结一切。
果然我放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