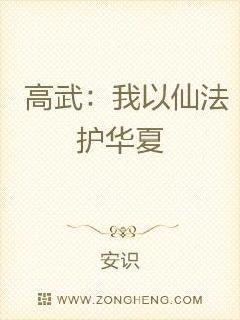极品中文>弦溺TXT > 第35頁(第1页)
第35頁(第1页)
那本該是屬於她的家庭。
公寓的信號並不好,滋滋的電流聲里,她隱約聽見溫藻嬌氣又略含不滿的「爸爸」,覺得是時候掛斷電話。
溫藻經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在國外生活上學的日常,活脫脫一個拜金名媛,惹來一大批艷羨的粉絲,似乎不懂何為低調。
「他們分明就是不想管你,提前把財產轉移,到國外過逍遙日子去了。」
6斯怡看見,忿忿不平,一語將窗戶紙戳破。
帶失而復得的女兒親親熱熱的出國,轉頭就將養女撇下。
雖然坊間傳聞溫氏破產蹊蹺,背後另有隱情,溫禧不願用最壞的惡意去揣度自己的父母,養育之恩亦無法一筆購銷。
「如果在國內過不好,就來國外吧。」
電話那端溫良明還在繼續,懸浮的關心說得頭重腳輕。
「沒事的,我很好。」
溫禧硬聲重複。
她不算鳩占鵲巢,卻始終失了立身的資本。
過往種種,譬如昨日死。溫禧作為獲利者,並沒有苛責他們的立場。
何況她還有當初還款的承諾沒有兌現。
「我把這些錢還清,也算是還清從前欠溫家的一份情,替他們博一份好的聲名。」
溫禧對錢向來沒有太多概念,從前一百萬甚至不夠她在拍賣會上胡鬧拍下的一件藏品,轉眼間變成難以企及的天文數字。
那時溫禧如夢初醒。
從前離家出走是胡鬧,是體驗,她不堪重負就可以時刻回歸,有家業為自己托底,現在後路被斷得一乾二淨。
時祺白日工作,黑夜練琴,想方設法地籌錢。
經濟的重擔像是源源不斷充氣的氣球,在他體內寄居、膨脹與爆炸。
真正擊潰她的,是從家裡的垃圾箱翻出那份被撕碎的維也納音樂學院錄取通知書,她一片一片地拼好,指尖顫抖,去擦難看的污痕。
是時祺騙她。
他說自己技不如人,在競爭者中遺憾落敗,從此可以好好留在國內,陪她一起生活。
在溫氏破產前,她好像突然有了不好的預感,時常在午夜驚醒。時祺怕影響她,練習時從不開燈,靜音踏板也壓到最底,琴蓋上壓滿了書,降低鋼琴的擴音效果。
她驚醒時,情緒也不穩,坐在床上莫名其妙地流淚。
「吵醒你了嗎?」少年的體溫覆身而上,溫柔地吻盡她眼尾的淚。
她本是嬌生慣養的富貴花,現在植根的土壤被盡數挖淨,就異化成了寄生獸,貪婪地蠶食他為夢想的充沛養分。
所以二十歲的溫禧,覺得自己無用如累贅,退出時祺的人生是最好的選擇。
而事實的確如此。
現在的他放手一搏,功成名就,站在萬眾俯的群山之巔。
掛上電話,溫禧心亂如麻,索性放任自己沉沉睡去。
手機屏幕卻忽然亮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