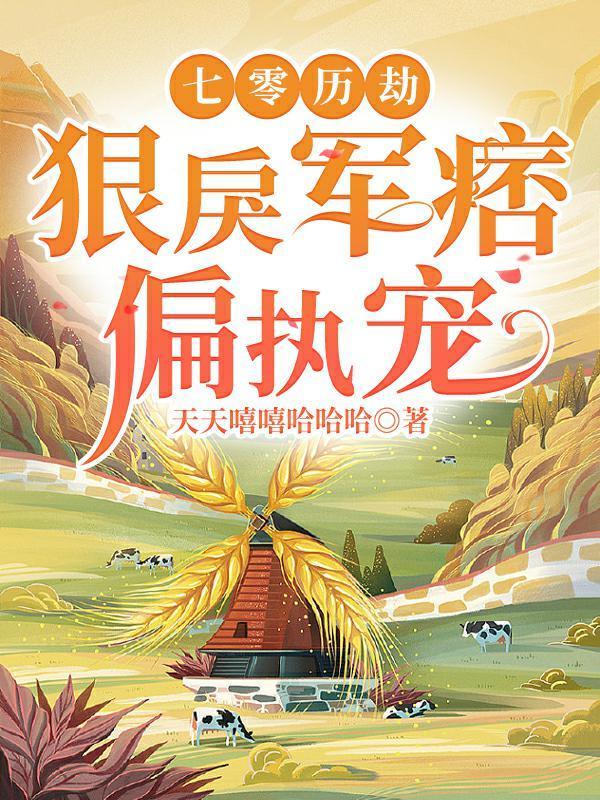极品中文>繁花第二部 > 第十一章(第1页)
第十一章(第1页)
壹
阿宝全家搬离的前夜,想不到小阿姨拎了半篮水红菱,忽然上门,见房内大乱,姐姐姐夫,闷声整理行李,深受刺激,当场与抄家人员大吵大闹,杀千刀跳黄浦,样样全来。阿宝娘哀求不止。值班监督人员,初以为小阿姨是保姆,最后认定神经病,明天就搬场,也就无心恋战。小阿姨揩了眼泪,摸摸阿宝肩胛说,阿宝,小阿姨来了,不要怕。第二日一早,小阿姨跟了阿宝全家,爬上了卡车,迁往沪西曹杨工人新村。阿宝朝蓓蒂,阿婆挥手。蝉鸣不止,附近尼古拉斯东正小教堂,洋葱头高高低低,阿宝记得蓓蒂讲过,上海每隔几条马路,就有教堂,上海呢,就是淮海路,复兴路。但卡车一路朝北开,经过无数低矮苍黑民房,经过了苏州河,烟囱高矗人云,路人黑瘦,到中山北路,香料厂气味冲鼻,氧化铁颜料厂红尘滚滚,大片农田,农舍,杨柳,黄瓜棚,番茄田,种芦粟的毛豆田,凌乱掘开的坟墓,这全部算上海。最后,看见一片整齐的房子,曹杨新村到了。
此种房型,上海人称“两万户”,大名鼎鼎,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沪东沪西建造约两万问,两层砖木结构,洋瓦,木窗木门,楼上杉木地板,楼下水门汀地坪,内墙泥草打底,罩薄薄一层纸筋灰。每个门牌十户人家,五上五下,五户合用一个灶间,两个马桶座位。对于苏州河旁边泥泞“滚地龙”,“潭子湾”油毛毡棚户的赤贫阶级,“两万户”遮风挡雨,人间天堂。阿宝家新地址为底楼4室,十五平方一小间,与1,2,3,5室共用走廊,窗外野草蔓生,室内灰尘蜘蛛网。一家人搬进箱笼,阿宝爸爸先捡一块砖头,到大门旁边敲钉子,挂一块硬板纸“认罪书”,上面贴了脱帽近照,全文工楷,起头是领袖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下文是,认罪人何年何月脱离上海,混迹解放区,何年何月脱离解放区,混迹上海,心甘情愿做反动报纸编辑记者,破坏革命,解放后死不认账,罪该万死。居委会干部全体到场,其中一个女干部拿出认罪书副本,宣布说,工人阶级生活区,一户反革命搬了进来,对全体居民同志,是重大考验,大家要振作起来,行动起来,行使革命权利,监督认罪人,早夜扫地一次,16号门口扫到1号,认罪人要保持认罪书整洁,每早七点挂,十八点收。阿宝爸爸遵命。干部看了看工作手册说,新社会到现在,还有大小老婆。阿宝爸爸指小阿姨说,是我内人妹妹,帮忙搬场。女干部拿出钢笔,记到工作手册里,一声不响。4室门窗前,立满男女看客,窗台上坐三个小囡,一切尽收眼底。阿宝一家四人,睽睽之下布置房问,大床小床,五斗橱摆定。2室阿姨讲苏北上海话说,妹妹,你家里,最要紧的东西,忘记掉了。阿宝娘不响。2室阿姨说,煤球炉子。阿宝娘惊讶说,此地用煤炉。2室阿姨说,嗯哪,洋风炉子,也可以滴,我才刚,一件一件看你家的家当,没得煤球炉子,也没得火油瓶子。阿宝娘愁容满面。3室嫂嫂讲苏北话说,用我家煤炉子,下点面条子,快的。2室阿姨说,还是用我家的,煤球炉,最要紧了,要便宜,买个炉胆子,用洋油火油箱子,自家做一个炉子,也可以。阿宝娘说,谢谢谢谢。3室嫂嫂说,不要忘记了,去办个煤球卡。阿宝娘说,谢谢。只有5室阿姨旁边看,一声不响,细腰身,笑眯眯有礼貌。小阿姨对阿宝娘说,阿姐放心,我会生煤炉,也会烧洋风炉,以前住虹口,就靠洋风炉子过日脚,不急的。阿宝娘一时讲不出话来。
“两万户”到处是人,走廊,灶披间,厕所,房前窗后,每天大人小人,从早到夜,楼上楼下,人声不断。木拖板声音,吵相骂,打小囡,骂老公,无线电声音,拉胡琴,吹笛子,唱江淮戏,京戏,本滩,咳嗽吐老痰,量米烧饭炒小菜,整副新鲜猪肺,套进自来水龙头,嘭嘭嘭拍打。钢钟镬盖,铁镬子声音,斩馄饨馅子,痰盂罐拉来拉去,倒脚盆,拎铅桶,拖地板,马桶间门砰一记关上,砰一记又一记。自来水按人头算,用电,照灯头算账,4灯收音机,等于15支光电灯,5灯收音机,算2o支光灯泡的度数。阿宝爸爸每天准时扫地,赶到单位报到,认罪书天天挂进挂出,回来迟,阿宝代收。阿宝娘漶浴,方台靠边,小阿姨拖出床底的大木盆来,到灶间拎了热水冷水。房门关紧,家家一样。男人赤膊短裤,立到灶间外面,一块肥皂一只龙头,露天解决,再进马桶间里换衣裳。黄昏,各家小板凳摆到大门外,房前房后,密密麻麻是人,凳面当饭桌,女人最后收作碗筷,为一家老小,汰了衣裳,拉出躺椅来,搭铺板,外面乘凉过夜。小阿姨说,此地宽敞,市区郊区,上海人乡下人,其实差不多。阿宝不响。小阿姨说,南京路天津路,倒马桶的房子,要多少有多少。阿宝说,嗯。小阿姨说,阿宝,要多交朋友,看见了吧,楼上1o室的小珍,一直朝此地看。阿宝说,小阿姨,还不够烦呀。小阿姨笑笑。吃了夜饭,万家灯火,阿宝走出一排排房子,毫无眷恋,眼看前方,附近是田埂,几棵杨柳,白天,树下有螳螂,小草,蝴蝶飞过,现在漆黑。阿宝闭眼睛,风送凉爽,树叶与蒿草香气,大蒜炒豆干,焖大肠的气味,工厂的化学气味。等到夜深返回,整幢房子静了,家家开门过夜,点蚊香,熏艾蒿,走廊闷热黑暗。2室是两张双层铁床,月光泻到草席,照出四只脚,四条小腿。自家房门挂了半块门帘,阿宝爸爸已经打地铺,阿宝娘与小阿姨已经人梦。家人距离如此之近,如此拥挤,如此不真实,但阿宝对小阿姨,依然心存感激。搬来当日,小阿姨领了阿宝,阿宝娘,到日用品商店买了煤球炉,火钳,脚盆,铅桶,蒲扇,四只矮凳。阿宝娘说,买两只吧。
小阿姨说,坐外面吃夜饭,两只凳不够。阿宝娘说,阿妹,我不习惯,不答应的。小阿姨说,外面吃饭,风凉。阿宝娘不响。小阿姨说,要跟邻居一样。阿宝娘说,要我坐到大门外,岔开两条大腿,端一碗粥,我做不出来。小阿姨说,苦头吃得不够,学习不够。阿宝娘说,十三点。小阿姨说,讲起来,以前我也算镇里有铜钿的二小姐,但吃苦比较早,人情世故早。阿宝娘说,结果呢,看错了男人。小阿姨说,是呀是呀,阿姐是享福人,房子好,男人好,现在呢,照样交“麻枯”运。阿宝娘不响。小阿姨说,放心,我会帮姐姐出头的。阿宝娘说,房子小,还是早点回乡吧。
小阿姨面孔一板说,啥,我跟派出所这个死人,已经离婚了呀,要我回乡,煤球炉,啥人来弄呢,每一户,照例轮流负责七天卫生,马桶间臭得要死,1室山东人,一家门天天吃韭菜大蒜洋葱头,熏得眼睛睁不开,啥人去弄。阿宝娘说,不要讲了。小阿姨说,楼上楼下,一共四只马桶间,下面通一条水泥槽,盖了四块马桶板,楼下负责打扫两块,每块要拖出来冲,揩,要到太阳里去晒,罗宋瘪三,苏联人搞的名堂,又臭又重,啥人做呢。阿宝娘说,不要讲了。小阿姨说,楼上几只赤佬,专门到楼下马桶问里大便,真自私,讲起来工人阶级。阿宝娘说,嘘。小阿姨说,烂污撤到马桶圈上,底下的水泥槽子里,月经草纸,“米田共”,堆成山,竹丝扫帚也推不动,真腻心呀。阿宝娘叹气说,实在不想走,再讲好吧。
礼拜天,大伯来到曹杨新村。思南路大房子扫地出门,一分为三。
大伯一家,迁到提篮桥石库门前厢房。婊婊因为皮箱事件,单位加大力度,忍痛与老公离了婚,跟了祖父单过,住闸北鸿兴路街面房。小叔一家三口,搬到闸北青云路亭子问。祖父定息取消了,大伯每月只二十九块三角,等于工厂学徒的满师标准,人口多,艰难。婊婊与小叔两家,单位工资一分不减,人少,还过得去。此刻,大伯靠了窗口,吃冷开水。
从解放直到“文革”,阿宝父母只逢阴历年,到思南路与大伯见一面,来往不多。阿宝父母不响。大伯说,看来看去,此地最好,窗外有野趣,里厢有卫生。阿宝娘说,也有难处。大伯说,人比人,是气煞人,弟弟的工钿再减,也有六十八块,弟妹是事业单位,工资八十四块,跟我不能比。
阿宝爸爸说,今朝来,有啥事体吧。大伯说,弟弟开口,还是硬邦邦,还不明白,两兄弟,其实是读书不用功,有啥好结果呢。阿宝爸爸不响。
大伯压低声音说,如果以前就有觉悟,到十六铺码头当小工,现在我跟弟弟,就是工人无产阶级,为啥缺觉悟呢。阿宝爸爸冷笑。大伯说,我一直做小开,全部老爸做主,我做“马浪荡”,东荡西荡,吃点老酒,看万有文库,美国电影,听评弹迷魂调。阿宝爸爸不响。大伯说,弟弟当初,读书太不专心,听了宣传,参加了组织,吃苦不记苦吧。阿宝爸爸不响。大伯说,如果认真读英文,中国公司先做起来,账做得好,春秋两季“点元宝”。阿宝说,啥。大伯说,也就是盘账,盘点盈亏,两兄弟再出洋,英国美国,先做跑街先生,再做“康白度”,也就是洋行买办,就不会有今朝。阿宝爸爸压低声音说,马上滚出去,出去。大伯说,脾气真古怪,已经全部落难了,啥火呢。阿宝娘说,阿哥难得来一趟,不要讲了。小阿姨说,吃了中饭回去,少讲两句。阿宝娘说,阿哥,衬衫先脱下来,房间里热。大伯说,弟妹,这件衣裳,阿哥脱不下来了,难为情的。
阿宝爸爸说,皮带抽过几趟,有伤了。大伯解开纽子说,运动到现在,只吃过一记耳光,还算好,每天写交代,问我黄金放啥地方,自家人面前,我食不兼味,衣不华绮,无所谓了。大伯脱了衬衫,里面一件和尚领旧汗衫,千疮百孔,渔网一样。大家不响。大伯说,开销实在难,我只能做瘪三,每日吃咸菜,吃芽豆,还要帮邻居倒马桶。大家不响。
小阿姨出门,买来两包熟食,台子拉到床跟前,端菜盛饭。五人落座。小菜是叉烧,红肠,葱烤鲫鱼,糖醋小排,炒刀豆,开洋紫菜蛋汤。
看到一台子小菜,大伯忽然滑瘫到凳下。阿宝拉起大伯。阿宝爸爸说,以前我坐监牢,也少见这副急腔。大伯喘息说,是我馋痨病作,胃痛了。小阿姨说,作孽,讲起来富家子弟,穷相到这种地步,快点吃。阿宝爸爸说,小阿姨,钞票太多对吧,为啥弄了七只八只,不是大客人,瞎起劲。小阿姨说,姐夫难得请兄长吃一顿饭,要面子吧,我不买账的,我是大脚娘姨,劳动人民,我买啥,就吃啥。阿宝娘说,轻点轻点。阿宝爸爸说,小菜弄得多,要吃伤的。大家不响,想不到此刻,大伯据案大嚼,已闷头吃进大半碗饭,叉烧红肠也吃了大半碗,仍旧不断拖到饭碗里,像聋甏,天吃星,嘴巴拼命动,恣吞恣嚼,不断下咽。小阿姨说,先吃口汤,慢慢咽,笃定吃,我早晓得,就买一只蹄髓,焖肉也可以,罪过罪过。大家不响,五个人这顿饭,吃得心惊肉跳。饭毕,大伯心定说j想想以前,本埠的上等馆子,我全部吃到家了,中饭夜饭,夜宵,公司菜,“新雅”茶点,煽蛤蜊,煽蜗牛,“老正兴”虾籽大乌参,划水,鲍肺,金银蹄,“大鸿运”醉鸡醉虾,样样味道好,但是吃下去,就统统不作数了,人的肚皮,十分讨厌,吃过就等于白吃,比不过这顿饭。小阿姨说,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吃死蟹,只只鲜。
阿宝娘正要开腔,只听外面敲门,进来几个居委会女干部。阿宝爸爸立起来。大伯也立起来。居委会女干部看看台面说,好的,小菜蛮多,今朝庆祝啥呢,国民党生日。阿宝娘说,是我老公的阿哥来了。居委会女干部看工作手册,看看大伯说,叫啥名字。大伯不响。居委会女干部说,资产阶级搬到了提篮桥,还要见面。大伯点点头。居委会干部说,老远过来,带啥东西来。大伯说,我空手。另一女干部说,拎包也不带。大伯说,是的。居委会女干部说,空手来,偷带几根金条银条,也便当,别到裤腰里,绑到脚膀上,一样坐电车。大伯苦笑说,各位干部,不要讲旧秤十六两一根大黄鱼,就是小黄鱼,黄鱼鲞,黄鱼籽,黄鱼身上金屑粒,金粉金灰尘,全部充公上交了。居委会女干部说,哭穷。大伯说,一句不假。小阿姨说,有啥多问的,饭也吃不太平。居委会女干部说,喂,不许插嘴。小阿姨说,我现在是正常吃饭,犯啥法。居委会女干部说,外地乡下户口,乡下女人,赖到上海不肯走,为啥。小阿姨跳起来说,来帮我的阿姐姐夫,我不犯皇法,叫派出所来捉呀,我的死腔男人,就是派出所的,张同志李同志,我认得多了,我打电话就来,试试看。居委会女干部一呆。小阿姨说,太气人了,逼煞人不偿命。另一个女干部说,喂,嘴巴清爽点。小阿姨忽然朝干部面前一横说,我怕啥,我怕抄家吧,抄呀,抄呀,抄抄看呀。阿宝与阿宝娘去拖。此刻,旁边的大伯忽然解开腰带,长裤一落到底。大伯说,请政府随便检查,我啥地方有黄金。
几个女干部,看见眼前两根瘦腿,一条黄的破短裤,立即别转面孔,低头喊说,老流氓,快拉起来。下作。
2
小毛进了门,端详一番说,到底是革命军人家庭,太平无事。沪生说,我爸讲,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小毛说,这幢大楼,最近跳下去多少人。沪生笑说,最近我爸讲,建国开头几年,也有一个跳楼高潮,当时的上海市长,一早起来吃茶,就问身边的秘书,上海的“空降兵”,昨天跳下来多少。小毛笑笑。沪生说,当时天天有人跳,现在的河滨大楼,天天也有人跳,心甘情愿,自绝于人民。小毛摇头。沪生说,这幢大楼,目前还算太平,最轰动的,是我中学隔壁,长乐路瑞金路口的天主堂,忽然铲平了。小毛说,我弄堂里,天天斗四类分子,斗甫师太,斗逃亡地主。
沪生说,我不禁要问,这种形势下面,阿宝跟蓓蒂,是不是有了麻烦,是不是要表态。小毛说,朋友落难,我想去看一看。沪生不响。两个人走到阳台。小毛说,还记得大妹妹吧。沪生说,记得呀,喜欢跳橡皮筋,大眼睛。小毛压低声音说,前天见到我,大妹妹就哭了,因为,大妹妹的娘,旧社会做过一年半的“拿摩温”,之后,就到其他纱厂做工,最后跟小裁缝结了婚,做家庭妇女,又做普通工人,因此瞒到了现在,运动来了,只要听见附近的锣鼓家生,呛呛呛呛一响,连忙钻到床底下,有一次躲到半夜,等爬出来,大小便一裤子,浑身臭得要死。沪生说,这是活该。小毛说,我对大妹妹讲,不要哭,嘴巴一定要闭紧,就当这个老娘,天生神经病,已经风瘫了,痴呆了,准备天天汰臭裤子,汰臭屁股,也不可以开口。沪生说,大家不禁要问,这样的社会渣滓,为啥不去自。
小毛说,“不禁要问”,大字报口气嘛。沪生笑笑。小毛说,可以自吧,不可以,隔壁弄堂,烟纸店的小业主,主动去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结果呢,打得半死,下个月,就押送“白茅岭”劳改了。沪生说,为啥。小毛说,讲起来简单,小业主的邻居,就是邻居嫂嫂,经常独霸水龙头,脾气一直刁,因此小业主跑到曹家渡,请一个道士做法,道士这一行,道行最深,香火叫“熏天”,吹笛子叫“摸洞”,鱼叫“五面现鳞”。沪生说,根本听不懂。小毛说,小业主一上门,道士心里想,“账官”来了,就是付账的人来了。小业主讲了嫂嫂情况,道士讲,搞这种“流宫”,最便当。小业主讲,啥意思。道士讲,这是行话,流宫,意思就是“女人”。
道士当场画了九张符篆,细心关照小业主,等邻居嫂嫂晾出三角裤,想办法,贴一张到裤裆里,三天贴一张,三三得九,贴九次,嫂嫂的脾气,就和顺了,浑身会嗲,等于宁波糯米块,重糖年糕,软到黏牙齿,样样可以随便,就是做眉眼,勾勾搭搭,搞腐化,样样答应。沪生摇摇头。小毛说,九张符策贴了,嫂嫂一声不响。有一日,嫂嫂到烟纸店买拷扁橄榄。
小业主讲,过来。嫂嫂讲,做啥。小业主讲,来呀。嫂嫂讲,啥意思。小业主霎一霎眼睛讲,到后间床上去,进去呀。嫂嫂讲,为啥。小业主讲,不为啥。嫂嫂讲,十三。小业主讲,身上有变化了。嫂嫂说,啥。小业主说,身体软了。嫂嫂讲,啥。小业主讲,下面痒了吧。嫂嫂一吓。
小业主讲,去后间,听见了吧。嫂嫂讲,下作坯。小业主讲,骚皮。嫂嫂讲,再讲一句。小业主不响。嫂嫂就走了。运动来了,曹家渡道士捉起来了,小业主吓了两夜,第三天到居委会自,龌龊事体兜出来,嫂嫂的老公,三代拉黄包车。沪生说,黄包车有三代吧。小毛说,加上三轮车,反正,男人太强横,上来对准嫂嫂,辣辣两记耳光,冲到烟纸店,柜台上面一排糖瓶,全部敲光,掴得小业主手臂骨裂,写认罪书,开批斗会,弄堂里看白戏的人,潮潮翻翻。沪生说,小业主绝对是“现行流氓犯”,人们不禁要问,大妹妹的娘,为啥不揪出来,旧社会专门欺压工人阶级的女工头。小毛说,这不对了,照我娘讲起来,“拿摩温”,就是纱厂女工的远房亲眷,热心人,介绍同乡小姊妹,来上海上班,也时常教唆工人动罢工,等于现在车间小组长,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沪生说,太反动了,不对了。小毛说,能说会道,手脚勤快,技术最过硬。沪生说,星星之火电影看过吧,“拿摩温”,东洋赤佬的帮凶,工人阶级太苦了。
小毛说,电影是电影,解放前,工人其实还可以,我娘做棉细纱车间,工钿不少,每个月,定规到“老宝凤”,买一只金戒指。沪生说,啊。小毛说,解放前,猜我娘买了多少金戒指,一手绢包,至少四五十只,大自鸣钟“老宝凤”银楼,专做沪西纱厂女工的生意,自产自销,韭菜戒,方戒,金鸡心,店里三个金师傅忙不过来,过年过节,光是戒指里贴梅红纸头,根本来不及,夜夜加班。沪生说,停停停,太反动了,小毛要当心,不许再瞎讲了。小毛说,我爸爸,英商电车公司卖票员,工钿也不少,上车卖票,每天要揩油,到“大世界”去混,去寻女人,每个月弄光,赌光,到结婚这天,我娘讲,耶稣眼里,人人欠一笔债,生来就欠,做人要还债,要赎罪,每天要祷告,我爸爸从此冷静下来,慢慢学好了。沪生说,乱讲了,宗教是毒药。小毛说,是呀是呀,所以我娘转过来,拜了领袖,比方我学拳,我娘讲,如果受人欺负,小毛不许还手,心里不许恨,领袖讲的,有人逼小毛走一里路,小毛就陪两里半。沪生说,还是像耶稣教。小毛说,我爸爸变好,完全因为信了宗教。沪生说,当心,这种瞎话,帮旧社会歌功颂德,走到外面去,牙关要咬紧,不许乱喷了。小毛说,这我懂的,人到外面,就要讲假话,做人的规矩,就是这副样子,就当我参考消息。
沪生说,下次来,还是先写信,或者打传呼电话,万一我出去呢。小毛说,如果白跑一趟,我可以去看姝华姐姐。
一小时后,两个人离开拉德公寓,走进南昌公寓,见姝华靠近电梯口拆信。姝华看看两人说,阿宝来信了。三个人凑过去看,信文是,姝华你好,看到这封信,我已搬到普陀区曹杨新村,房屋分配单送到了,卡车明早就开。你如果方便,经常去看看楼下蓓蒂,情况不大好。你以前常讲陈白露的话,现在我已经感觉到了,我觉得,天亮起来了,我也想睡了。祝顺利。阿宝。大家不响。小毛说,最后几句,这是要自杀了。沪生说,我不禁要问,这种形势下面,阿宝的态度呢,彻底划清界限,还是同流合污。姝华说,沪生,大字报句子,少讲讲。三人出公寓,走到思南路上。阿宝祖父的大房子,红旗懒洋洋,门窗大开,里面碌乱,拆地板的拆地板,掘壁洞的掘壁洞。姝华说,工人阶级抄家,最看重红木家具,金银细软,踏进房间来抄,就算碧落黄泉,也要搜挖到底。沪生说,学生抄家呢。姝华说,高中生,大学生走进门,带了放大镜,注意文字,年代,人名,图章,图画,落款,一页页仔细翻书,看摘引内容,划线,天地部分留字,书里夹的纸条,所有钢笔,铅笔记号,尤其会研究旧信,有啥疑点,暗语,这是重点,中文外文旧报,旧杂志,一共多少数量,缺第几期,剪过啥文章,全部有名堂,最有兴趣,是研究日记簿,照相簿,每张照片抽出来,看背后写了啥,只要是文字,记号,照片,看得相当仔细。小毛说,学生抄家,一般就是偷书,弄回去看,互相传,工人抄家,是揩油,弄一点是一点,缺一只皮箱,少一只皮包,小意思。沪生不响。小毛说,厂里办抄家展览会,看不见一本书,账簿多,资本家变天账。姝华说,摆满金银财宝,雕花宁式床,东阳花板床,四屏风,鸦片榻,面汤台,绫罗绸缎,旗袍马褂,灰鼠皮袍子。小毛说,工人喜欢珍珠宝贝,大小黄鱼,银碗银筷,看得眼花落花,骂声不断,表面喊口号,心里闷。沪生说,乱讲了,这是阶级教育场面。姝华说,工人,等于农民,到城里来上班,想不到错过了农村“土改”,分不到地主富农的一分一厘,享受中式眠床,红木八仙台,更不可能了,听老乡渲染当年场面,憋了一口气,现在,好不容易又碰到抄家,排队看了展览会,不少人心里就怨,问题不断,已经彻底清算了资产阶级,为啥不立即分配革命成果呢,乡下城里,过去现在,政策为啥不一样,不公平。沪生说,只会强调阴暗面。姝华说,农业习惯,就是挖,祖祖辈辈挖芦根,挖荸荠,挖芋艿,山药,胡萝卜白萝卜,样样要挖,因此到房间里继续挖,资产阶级先滚蛋,扫地出了门,房子就像一块田,仔细再挖,非要挖出好收成,挖到底为止,我爸爸是区工会干部,这一套全懂。沪生说,不相信。姝华说,不关阶级成分,人的贪心,是一样的。
小毛说,宋朝明朝,也是一样。姝华说,上海刚解放,工会里的积极分子,就向上面汇报,打小报告,工人创造了财富,自家差不多也分光了,农民伯伯走进工人俱乐部,一看,脚底下地毯,比农家的被头还软,太适意了,中沪制铁厂,工人拒绝开会学习,食堂里,肉饼子随地倒,每月每人水果费,一天吃四五瓶啤酒,穿衣裳,起码华达呢,卡其布,每个工人有西装,不少人吃喝嫖赌,九个工人有小老婆,十几个工人有花柳病。
小毛说,啥。姝华说,厂里每月,要用多少医药费。沪生说,极个别现象,强调领导阶级阴暗面,有啥用意呢。小毛说,我爸爸讲,抄家相等于过春节,厂里人人想参加,矛盾不少,我师父厂里,也办展览会,雕花床,真丝被头,绣花枕头,羊毛毯,比南京路“床上用品公司”,弹眼多了,结果,出了大问题。姝华说,不稀奇的,大概有人偷皮箱,偷枕头。小毛说,是偷女人。姝华面孔一红。小毛说,半夜里,值班男工听到床里有声音,绣花帐子,又深又暗,男工钻进去看,窗口爬进一个夜班女工,咽进丝绵被头讲梦话,磨牙齿,结果三问两问,男工就压迫女工了。姝华摇手说,小毛,不要讲了。沪生说,后来呢。小毛说,后来。姝华说,小毛。沪生说,工人的败类。小毛说,第二天一早,工人领袖带了群众队伍,进来参观,排队走到床前头,讲解员拿了一根讲解棒,朝绣花被头一指,刚要讲解,女工咽醒了,翻过身来,睁开眼睛讲,做啥。工人领袖一吓讲,啊。女工说,做啥。工人领袖说,死女人,快爬起来。女工不响。
工人领袖仔细一看说,啊,四车间落纱工“小皮球”嘛,不要命了,“掮纱”生活,啥人顶班。女工说,我腰肌劳损,不做了。工人领袖说,快起来,不要面孔的东西。女工不响。工人领袖说,听见吧。女工说,我不起来,我享受。工人领袖说,简直昏头了,这是啥地方。女工说,高级眠床呀。工人领袖说,展览会懂不懂。女工说,展览为啥呢,现在我的体会,太深了,我住“滚地龙”,睏木板床,背后一直硬梆梆,这一夜不睏,有体会吧。工人领袖说,起来起来,大腿也看到了。女工脚一动,一拉,等于让大家参观抄家物资,穿了一条白湖绸宽边绣花咽裤。女工说,资本家小老婆可以穿,可以胭,我为啥不可以,阶级立场有吧。姝华不耐烦说,好了好了,结束,不要讲了,完全嚼舌头了。小毛笑笑,沪生不响。
三个人转到皋兰路,蓓蒂的房门关紧。姝华招呼几声,蓓蒂,蓓蒂。无人答应。走上二楼,看见阿宝房里一片狼藉,果然已经搬走了。几个工人撬地板。姝华说,家具留了不少,曹杨新村,一定是小房间。工人说,进来做啥。三个人不响。沪生说,乱挖点啥。工人说,关依屁事。沪生说,我是红永斗司令部的。工人打量说,为啥不戴袖章。小毛说,调换袖章,经常性的动作,司令部新印阔幅袖章,夜里就。工人说,走开好吧。沪生说,我有任务。工人说,此地已经接管了。小毛说,老卵。工人说,小赤佬,嘴巴清爽点。小毛上去理论,沪生拉了小毛下楼。姝华叹息说,真不欢喜跟男小囡出门,吵啥呢。三人坐到小花园鱼池边,水里不见一条金鱼,有一只破凳子,一只痰盂。姝华说,善良愿望,经常直通地狱。沪生不响。姝华说,庸僧谈禅,窗下狗斗。沪生说,啥。姝华说,我现在,只想钻进阁楼里,关紧门窗去做梦。小毛说,阁楼关了窗,太阳一晒,要闷昏的。姝华说,听不懂就算了。沪生看看周围说,少讲为妙,走吧。小毛立起来说,现在,参加“大串联”的人不少,我想去散心。
3
停课闹革命,沪生的父母,热衷于空军院校师生造反,一去北京,几个礼拜不回来。姝华父母,“靠边站”,早出夜归。沪生不参加任何组织,是“逍遥派”,有时跟了姝华,出门乱走。瑞金路长乐路转角,原有一所天主堂,名君王堂,拆平的当天,姝华与沪生在场观看。某一h,两人再次经过,这个十字路口空地,忽然搭起一座四层楼高的大棚,据说,是油画雕塑院的工棚。两人走进满地狼藉的长乐中学,爬上四楼房顶,朝隔壁这座大棚张望,工棚里相当整洁,竖了一座八九米高的领袖造像,通体雪白,工作人员爬上毛竹架子,忙忙碌碌,像火箭射场的情景。姝华说,我记得君王堂,有两排圣徒彩塑,身披厚缎绣袍,可惜。沪生说,拆平天主堂,等于是“红灯照”,义和团造反,我拍手拥护。姝华冷淡说,敲光了两排,再做一尊。沪生一吓说,啥。姝华不响。沪生轻声说,姝华,这是两桩事体,对不对。姝华不响。沪生说,即使有想法,也不可以出口的。姝华说,我讲啥了。沪生不响。两个人闷声下楼,踱出校门。姝华说,此地,我不会再来了。沪生说,不开心了。姝华不响。
长乐中学大门,路对面是向明中学校门,中间为瑞金路。沪生想开口,一部41路公共汽车开过来,路边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扑向车头,只听啪的一声脆响,车子急停,血溅五步,周围立刻看客鲤集,人声鼎沸。沪生听大家纷纷议论,寻死的男人,究竟是向明老师,还是长乐老师,基本也听不清。姝华目不斜视,拉了沪生朝南走。两人刚走几步,沪生忽然说,这是啥。姝华停下来。沪生现,路边阴沟盖上,漏空铁栅之间,有一颗滚圆红湿小球,仔细再看,一只孤零零的人眼睛,黑白相间,一颗眼球,连了紫血筋络,白浆,滴滴血水。姝华跌冲几步,蹲到梧桐树下干呕。沪生也是一惊,过去搀起姝华。姝华微微抖,勉强起身,慢慢走到淮海路口,靠了墙,安定几分钟。
两人垂头丧气,朝东漫走,最后转到思南路。这一带树大,相对人少,梧桐叶落,沿路无数洋房,包括阿宝祖父的房子,已看不到红旗飘飘,听不到锣鼓响声,沸腾阶段已经过去,路旁某一幢洋房,估计搬进了五六户陌生人,每个窗口撑出晾衣竹竿。两人坐到路边,一声不响。姝华说,人与人的区别,大于人与猿的区别,对吧。沪生不响。姝华说,罗兰夫人临死前讲,自由,有多少罪恶,假尔之名实现。沪生说,我不禁要问了,姝华一直喜欢背书,背这种内容,有意思吧。姝华说,秋天到了,人就像树叶一样,飘走了。沪生说,春夏秋冬,要讲林荫路,此地是好,上海有一棵法国梧桐,远东最大悬铃木,晓得吧。姝华不响。沪生说,中山公同西面,又粗又高,讲起来法国梧桐,又是意大利品种。姝华不响。沪生说,租界时期,这条路叫马思南路,为啥呢。姝华说,听说是纪念儒勒马思南,法国作曲家。沪生说,我只晓得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姝华说,马思南的曲子,悲伤当娱乐,全部是绝望。沪生说,姝华不可以绝望。姝华说,此地真是特别,前面的皋兰路,租界名字,高乃依路,高这个人,一生懂平衡,写喜剧悲剧,数量一样,就像现在,一半人开心,一半人吃苦,再前面,香山路,旧名莫里哀路,与高乃依路紧邻,当年莫里哀与高乃依,真也是朋友,但莫里哀只写喜剧,轻佻欢畅,想想也对,一百年后,法国皇帝上断头台,人人开心欢畅,就像此地不远,文化广场,人山人海,开会宣判,五花大绑,标准喜剧。沪生说,又讲了,又讲了。姝华不响。沪生说,路名就要大方,北京路,南京路,山东路,山西路。姝华说,前阶段吵得要死,每条马路要改名,“红卫路”,“反帝路”,“文革路”,“要武路”,好听。沪生笑笑。姝华说,法国阵亡军人,此地路名廿多条,格罗西,纹林,霞飞,蒲石,西爱咸思,福履理,白仲赛等等,也只有此地三条,有点意思。沪生说,不如小毛抄词牌。姝华说,啥。沪生说,清平乐,蝶恋花。姝华不响。沪生低声说,小毛认得姝华之后,暗地抄了不少相思词牌,浮词浪语,比如,倦寻芳,恋绣衾,琴调相思引,双双燕。姝华面孔一红,起身说,我回去了。沪生说,好好好,我不讲了,不讲了。姝华跟了沪生,闷头朝前走。
两个人转进了皋兰路,也就一吓。阿宝家门口,停了一部卡车。沪生说,会不会,阿宝又搬回来了。姝华说,是蓓蒂要搬场了。两人走近去看明白,是外人准备迁来,一卡车的男女老少,加上行李铺盖。司机正与一个干部交涉,阿婆与蓓蒂,立于壁角,一声不响。干部说,居民搬场,要凭房屋调配单,我只认公章。司机一把拉紧干部衣领说,啥房管局,啥公章,现在是啥市面,懂了吧。干部说,不懂。司机说,最高指示,就是抢房子。干部说,胆子不小,毛主席讲过吧。男人说,现在就打电话去问呀,外区,全部开始抢了,新旧房子,全部抢光。此刻,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压低声音对干部讲,真的抢了,沪西公交三场附近,一排新造六层楼公房,五六个门牌,全部敲开房门,抢光,底楼八九家空铺面,也坐满人了。干部强作镇静说,此地是市中心,不是外区,不可以。卡车上的女人说,阿三,拳头上去呀,有啥屁多哕嗦的。房管干部跳起来说,无法无天了,啥人敢动,我不吃素的,试试看,我马上调两卡车人马过来,我也是造反队,我可以造反。干部讲完,即与同事密语,随后说,立刻派人来,快一点。同事转身就跑。干部拖来一只靠背椅,坐到卡车前面。司机与家属见状,忽然不响了。大门旁的阿婆,面有菜色,蓓蒂头蓬乱,一声不响,几次想奔到姝华身边来,阿婆拖紧不放。时间分分秒秒过去,司机转来转去,与车厢下来的几个男人聚拢,低声商议。
沪生觉得,随时随地,卡车的厢板,忽然一落,这批男女直接朝房子里冲。但是,卡车动了。干部起身,拖开椅子。司机跳上车踏板说,娘的起来,下趟再算账,房子有的是。司机拉开车门,钻进去,车子一动,车厢里的痰盂面盆,铁镬子铅桶一阵乱响。一个女人朝下骂道,瘟生,臭瘪三,多管闲事多吃屁。卡车出了马路,绝尘而去。
沪生松一口气,上去招呼阿婆,蓓蒂。姝华说,还好还好。干部说,好啥,做好思想准备,现在抢房子最多了。沪生看看蓓蒂,阿婆说,苦头吃足。姝华说,蓓蒂好吧。阿婆说,蓓蒂自家讲。蓓蒂不响。四个人走进房问,满地垃圾。阿婆说,我带了蓓蒂,参加“大串联”,刚刚回来。
沪生笑说,小学生,跟一个小脚老太去串联。蓓蒂说,来回坐火车,不买票。阿婆说,我等于逃难。蓓蒂说,我到哪里,阿婆跟到哪里,讨厌吧。
阿婆说,我要为东家负责,有个叫马头的赤佬,一直想搭讪蓓蒂,我心里气,这天呢,马头跟几个中学生,想拐带蓓蒂去北京,蓓蒂是小朋友,我根本不答应,蓓蒂就吵,奔进北火车站,我一路跟,北火车站人山人海,人人像逃难,蓓蒂哪里寻得到马头。蓓蒂说,人太多了,阿婆还想拉我,人就像潮水一样推上来了,火车开了门,后面一推,我跟阿婆跌进车厢,刚坐稳,人就满了。
阿婆说,人轧人,蓓蒂想小便,寻不到地方。蓓蒂白了阿婆一眼。阿婆说,等到半夜里,火车开了,第二天开到南京浦口,我想到外婆,眼泪就落下来,大家等火车开进长江摆渡轮船,一次几节车厢,慢慢排队,看样子,过长江要等半天,我肚皮太饿了,拖了蓓蒂下来,搭车进了南京城,蓓蒂跟我一路穷吵,想去“红卫兵接待站”,以为碰得到马头,据马头讲,进了接待站,就可以免费吃饭,两个人走到半路,我看到一扇大门,上面写,本区支持大串联办公室,不少人进进出出,我拖了蓓蒂进去,十多个小青年,戴了红卫兵袖章,围拢一个写条子的干部,一个小青年讲,接待站吃不到饭,我饿了一天了。另一个讲,我饿了两天了。干部讲,不要吵,一个一个讲,住南京啥地方,哪里一个街道接待的。小青年讲了街道地方,干部两眼朝天,想了一想,落手写几个字讲,好,凭这张白条子,到接待站西面,数第三家店,49号,小巷子隔壁,有一家“奋斗”饮食店,凭我条子,领六只黄桥烧饼,两碗面,以后问题,接待站逐步会解决。小青年欢天喜地,拿了条子轧出来。我一看急了,拖了蓓蒂,就朝里钻,朝里轧,同志,同志呀,干部同志呀,此地还有饿肚皮的红卫兵,一老一小,上海来的,要领烧饼,领两碗面,我可以节省一点,菜汤面,素浇面就可以了,帮我写,帮我写条子呀,批一张条子呀。想不到,周围小青年,是一批坏学生,立刻骂我,死老太婆,老神经病,年纪这样大,好意思骗吃骗喝,马上轰我出来,蓓蒂当场就哭了,两个人出来,路上乱走,幸亏蓓蒂捏有四斤全国粮票,买了一对黄桥烧饼,我让蓓蒂吃糖藕粥,两人分一碗鱼汤小刀面,唉,看见南京城,我落了眼泪,准备去天王府里拜一拜,蓓蒂胆子不小,还想去北京,去寻马头。我讲,敢。
眼睛不识宝,灵芝当蓬蒿。以前此地,名叫太阳城,天安门有多少黄金,我不明白,南京天王府里,现成的金龙城,一样是金天金地金世界。沪生说,广西打到南京,禁止人民姓王,书上有王,就加反犬旁,一路抢杀,金子堆成山。阿婆说,结果又听讲,天王府,早已经烧光了,造了一间总统府,啊呀呀呀,作孽呀,我头昏了,真是乱世了,以前南京太阳城,就有天朝门呀,高十几丈,城墙高三丈,金龙城里,黄金做的圣天门,黄金宝殿,看见了洪大天王爷爷金龙宝座,我一定要磕头的。蓓蒂说,好味,不要讲了。姝华说,这是真的。阿婆说,大天王爷爷宝殿旁边,蹲有黄金大龙,黄金大老虎,黄金狮,黄金狗。蓓蒂说,金迷。阿婆说,喜欢黄金,天经地义,虽有神仙,不如少年,虽有珠玉,不如黄金。蓓蒂捂紧耳朵说,好了,不要讲了。阿婆说,接待站,不一钱一厘金子银子,一只铜板,一只羌饼也拿不到,还要赶我出门,真是恨呀,如果我身上有黄金,就算是逃难,也不慌了。沪生说,拿出金银去买饭,肯定吃官司。姝华说,阿婆,不要再讲了,遇到陌生人,千千万万,不可以再讲磕头,不可以再讲南京北京黄金,圣天门,天安门,要出事体的。阿婆说,我还有几年活头呢,是担心蓓蒂呀。大家不响。阿婆说,马头讲过,可以保牢蓓蒂的钢琴,这是瞎话。蓓蒂说,我答应马头,钢琴可以寄放到杨树浦,工人阶级高郎桥。阿婆死也不肯,怪吧。姝华说,这是做梦,现在太乱了,随便几个人,就可以来搬来夺。阿婆不响。
姝华叹息说,这副样子,确实是悲伤当娱乐,一半喜剧,一半悲剧。沪生不响。请牢记收藏,&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