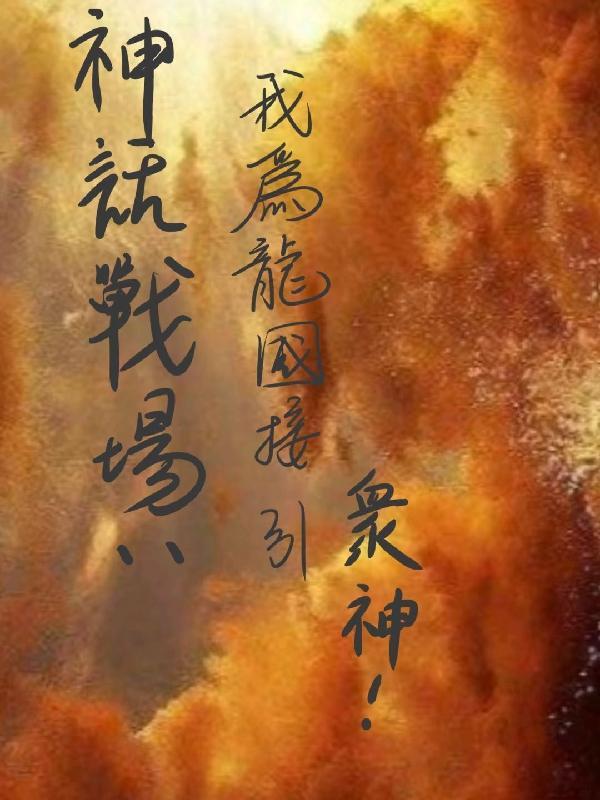极品中文>妹妹你别走叫什么名字 > 第40章 爱得仓促(第1页)
第40章 爱得仓促(第1页)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
晚饭是在外面吃的,一家人回到家已经是亥时三刻了。
平日里这个时间大家早都睡熟了,今天是因为春节期间城中有夜市,大家才能玩到这么晚。
孩子们各自回房休息了,青岑安夫妻俩梳洗之后也回房躺下了。
想起白日里的种种,青岑安低低开口问:“耘娘,今日岳母可是与你说了什么,使你感到为难了?”
“你怎么这么问?”
“你我同床共枕十几载,早已知己知彼,你的情绪如何,我自然感受得到,白日里孩子们都在,又在街市上,我也不好开口问。”
“娘确实跟我说了个事,但我没答应。”
“什么事?”
“娘的意思,大概是大姐家的三个女儿可怜,又因为父母和离一事,以后怕是也不好说人家,于是有了亲上加亲的想法。”
“亲上加亲?意思是让嫁到咱们家来?”
青岑安皱了皱眉,这岳母平日里挺睿智的一个人,怎么会想出这种馊主意?
苗贞耘自然听出了青岑安的不满,别说他了,她自己都不乐意,大姐家三个女儿可怜又不是自己一家害的,凭什么要自己一家替她们承担后果。
再者,苗贞耘可没忘记那日从娘家回来之后二儿子找她说的那些事,那三个小姑娘性子古怪,几个儿子都是一副退避三舍的模样,怎么可能愿意娶她们进门。
也不知娘这主意是怎么打到自家孩子头上的,不对,或许,这出主意的另有其人。
难怪啊,难怪那日大姐用那奇怪的目光审视自己的几个儿子,原来她从那时就打起了自家儿子的主意啊。
她这算盘打的挺响亮,算盘珠子都崩脸上了。
原本还觉得有些对不起爹娘的苗贞耘,瞬间就怒了,苗贞茹真是好算计,自己躲在后面出馊主意,让老娘替她出头,一副小人行径,真是让人倒胃口。
大半夜的,苗贞耘差点被恶心得吐出来,倒是把旁边的青岑安又吓了一跳。
媳妇要是再怀上一个,他爹非得扛着锄头从村里冲出来将他打成孙子不可,别看他一把年纪了,对他爹的畏惧依旧不减当年。
想当年,在自家农田里劳作的爹被两头从旁边树林冲出来的野猪袭击,但他并没有慌乱,而是拿起他手上唯一的武器——锄头,当场与两头野猪搏斗了起来,经过将近两刻钟的殊死搏斗,两头手无寸铁的野猪被他爹用锄头斩于脚下。
因为以一己之力斩杀了两头野猪,他爹名扬方圆十里八村,人送外号“野猪刽子手”。
自那以后,青岑安兄弟几人看见自家爹拿起锄头,都有些憷。
没办法啊,那锄刃能锄地,也能斩野猪,那锄头炳能坐能卧,也能打人,日日被汗水浸湿的锄头柄打人可疼了,那是青岑安不敢回忆的噩梦。
苗贞耘好不容易从恶心反胃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就见身边的男人抖了抖。
“你也被恶心到了?”
“不是,我只是想起来一些童年阴影,身体不受控制罢了。”
“哦,那咱们还真是难夫难妻。”
青岑安将人搂进怀中,轻声道:“别瞎说,咱们怎么会是难夫难妻,咱们夫妻如此恩爱,是要白头到老的。”
“你就知道贫嘴。”
“我的嘴只跟你贫。”
苗贞耘佯装嫌弃的别过脸,青岑安就凑过去,拉着她的手,一个往回抽,一个就攥的更紧,还信誓旦旦说手太冷了我给你暖暖。
也不知是真的暖手还是也暖了别的什么,总之夫妻俩很快就就闹成一团,大红的鸳鸯被子在黑夜中起起伏伏,像一阵阵红色的波浪在翻腾。
被尿意憋醒了的青描夏,一睁眼看见的就是这么个少儿不宜的场景,她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