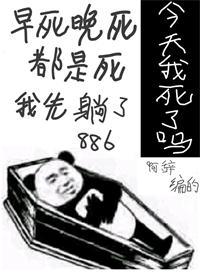极品中文>爱人他嘴硬心软txt免费阅读 > 第 11 章(第2页)
第 11 章(第2页)
周望川笑道:“她是在问,你为什么这些天不来看她。”
“她问,还是你问?”
商暮似乎是好一些了,声音不再断断续续。但仍然微弯着腰,右手在腹部有一下没一下地揉摁着,他按得用力,衣服在腹前绷紧,勾勒出漂亮的腰线。
周望川道:“去开点药吧。”
四喜跳到两人中间,亲昵地用脑袋蹭着,这边蹭一下,那边蹭一下,一脸享受。
商暮摇摇头:“没事,休息一晚就好了。”他摸了摸四喜的下巴,四喜立刻舒服地咕噜咕噜。
“好了,我们走吧。劳烦学长送我回宿舍。”商暮撑了下座椅扶手,站起身来。
周望川扶着他走到宿舍门口,正要离开,商暮却又叫住他。
“学长。”
“就算我是……”商暮脸色仍然苍白,但他露出了一个近乎甜美的笑,脸上漾着两个小梨涡,“我也是1。”
门口的风铃声唤回了周望川的意识,现在他当然已经知道,当年商暮并没有和那个男生发生什么,那天的酒店里,只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实践而已。
当年,商暮为了和他实践,才选择和他在一起。拖拖拉拉到现在六年,两人就这个问题争吵过无数次,每一次都不欢而散。争吵的频率越来越高,争吵的架势越来越大。
周望川已有预感,他们迟早会因这件事而散。
为了实践而在一起,耗了六年,现在又将为不能实践而分手。
一次次的争吵,一次次的冷语,一次次的挂断电话,一次次的拉黑删除。商暮是早已受够了他。
他只能用无微不至的关怀,用鞍前马后的照顾,来搏那一丝心软和留恋。
可结果注定失败。
周望川慢慢喝完了杯中酒,起身离开了包间。
桌上的菜肴失色冷去。玫瑰花束知道自己只是没人要的残花败柳,不复鲜活,蔫蔫地垂下头。
走出餐厅时,黑胶唱片送来了最后一句歌词。
“Causeyouweren’tminetolose……”
你从未属于过我,便又谈何失去。
周望川去医院值班到凌晨。回到家里,果然空无一人。
他拨通了电话,只有一串机械的忙音。
正思索着该怎么办,门却突然响了,商暮走了进来,看也不看他一眼,径直去卧室收拾了几件衣服。
周望川跟在他身后,轻声道:“很晚了,休息吧。”
商暮并不理他,只把衣服装入包中。
“我错了。”周望川说。
商暮拎着包往门口走,脚步不停。
周望川叹了口气:“你不想见到我,我就去医院,你留下来早点休息吧。”
商暮终于停下脚步,转身看向他,声音一如既往的冷:“别介,我承担不起您的好心。”
门被打开,又被重重地关上。
周望川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去了书房。太师椅空空荡荡,孤独地立在月光中。
昨天这个时候,他们在这张椅子上温言细语,亲密缱绻,不到一天的时间,一切都变了。
又过了一会儿,周望川拨通了母亲程云萱的电话,请她帮忙确认商暮的安全。
程云萱很快回了电话:“我问他啦,他说在酒店,就要睡下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又吵架了?”
周望川说:“没事儿,妈,你也早点休息。”
程云萱说:“年轻人嘛,吵架是正常的,明天好好谈谈,说开了就好了。”
电话挂断后,周望川来到窗边。初秋的月亮是浅淡的,有些残缺,有些寂冷,孤零零地挂在窗户那头,像一朵粘在窗上的霜花。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