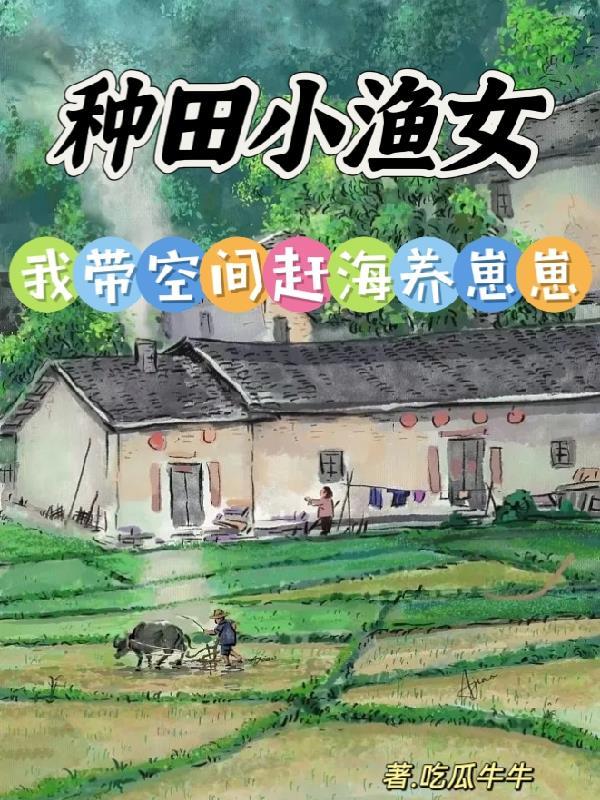极品中文>煞神方位在东方是什么意思 > 第34页(第1页)
第34页(第1页)
红盖头下扮新娘的欢喜回忆着刚才达步陵昊揪着他耳朵吩咐的话,欲哭无泪。
“听着,行礼的时候不许行全礼。本王眼睛尖着呐,敢占本王的便宜,小心你的脑袋。”
要不是碍于主子的威严,谁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活,摊上这么一个主子真没办法。
几大叩首之后,几位喜娘笑眯眯地领着新人入洞房。原以为新郎是煞神收的男宠,到时煞神肯定会揭下盖头招待客人。如今看新郎是乾王,现场谁还敢让新娘摘下盖头让大家仔细瞧瞧,那些憋足了劲来看美女的人大失所望。
到了后院没外人的地方,达步陵昊突然抬起一脚,狠狠地踢在欢喜屁股上。然后挤出灿烂的笑容,回前厅待客。
“爷,我没全跪。”欢喜扯下红盖头,委屈地揉着屁股。
达步陵昊头也不回地摆摆手:“哼,谁叫你冒充我家娘子。”
虽是达步陵昊自己出的主意,但一想起身旁本该是沈圆月的位置被欢喜占着,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哪是个憋得住气的人,自然不顾自己才是罪魁祸首冲欢喜撒起了火。
呸,真是蛮不讲理,欢喜暗骂。
到了前厅,客人们纷纷涌上来向他祝贺。这亲成得并不名正言顺,就连拜堂时用新娘子也是假冒的,但达步陵昊的脸皮是何等的厚,坦然接受着众人的祝福。在他心里沈圆月早已等同与乾王妃,乾王妃当然只能嫁给乾王。今日沈圆月正在气头上,若是用心哄好她,好日子又不知要推到什么时候去。他俩已经拖了太久,实在不应该再浪费时间。只要新娘确确实实是沈圆月,其他地方掺点假有什么要紧。他和沈圆月就算成亲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达步陵昊从未这么开心过。他来者不拒,与客人推杯换盏喝到满脸红光。酒席散后客人纷纷告辞离去,欢喜这才忐忑不安地扶着他往新房走。
和外人串通做了这么出格的事情,沈开很不安。他早在宴会进行时就跑到兵器库找了个铜盾牌,此刻缩头缩脑地跟在达步陵昊身后。娘不会杀他,但达步陵昊无疑有生命危险。万一发生不测,有这个盾牌还能挡一下让达步陵昊逃生。
看沈开和欢喜眉头紧皱的样子,达步陵昊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也知道自己做的事足以将沈圆月惹毛,可他一点也不害怕。
他的命已经和沈圆月系在一起。沈圆月若杀他,证明心中没有他。既是如此,死有何惧?反正他同沈圆月成亲的消息已经传开,就算他死,沈圆月也再甩不开乾王夫人的头衔,这种情况光是想想就无比开心。沈圆月若不杀他,那还等什么,自是马上共享闺房之乐,努力让沈圆月忘却男宠逃亡的不快。
无论怎样此生都再也无憾,此时此刻,他只想快点走到沈圆月房间,见到他的爱人。
天色已暗了下来,沈圆月屋里仍然黑漆漆的,没有一丝光亮。风轻轻地吹着,门口两盏鲜红的囍字灯笼缓缓晃动,摇碎了一地艳丽的光影。
达步陵昊一站到门前就毫不迟疑地抬手敲了敲门。
没人应声。
“圆月。”他轻声喊,“开门,是我。”
喜娘拎着红灯笼,匆匆忙忙地从院外跑过来,微微一欠身:“禀王爷,夫人整天都呆在房里没出声。”
依沈圆月的性子,天不说话也不成问题。达步陵昊并不着急,向身后勾勾指头:“影卫,打开门闩,要轻轻的。”
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厮从院外走进来,掏出一个铁片样的东西,走到门前沿着门缝轻轻一拨弄:“爷,开了。”说完又低头让开。
达步陵昊转身拿过喜娘手里的红灯笼,轻轻推开了房门:“圆月,我进来了。”
屋里还是没声音,从外面往里面看墨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没人答应就算是答应了,达步陵昊拎着灯笼大步流星地走了进去。
刚走两步,脚下踩到了水渍状的液体兀地一滑,眼看就要跌倒。惊慌中他左手一抓,无意间扣住了一个人的肩膀。等定□将灯笼凑到那人面前,鲜红的烛光赫然对上了一张描着鲜艳妆容的煞白脸庞。凌乱的长发后藏着一双茫然的眸子,眸中没有任何光亮,只剩一片荒野般的死寂。
“圆月?”达步陵昊不确定地问。
话音刚落,沈圆月闭上眼睛一头栽倒。他慌忙将其搂住,手上和胳膊上却沾上了什么湿润的滑腻东西。提起灯笼一看,手掌上尽是血红。
“圆月!”
灯笼滚落在地,腾地燃烧起来,吞噬了灯笼上大红的喜字。熊熊火光照亮了整间屋子,地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血迹。
沈圆月身上的伤口全是发簪刺的,都不是很深。黄金发簪攥在沈圆月自己手里,怎么扳也拖不下来,还是胡太医在她手上扎了一针才将簪子抽出。待胡太医替她包扎完,达步陵昊坐到床边,专注地盯着她白瓷般的脸颊问:“太医,她并未伤级根本,怎么还不醒?”
身上的病痛好治,心病难医。这煞神怕是因为真正的新郎跑路,一时想不开气成失心疯了。患了失心疯,有人下一刻就好了,有人一辈子也不能好。不能说实话,胡太医只能往好听的说:“定北候的外伤并无大碍,估计是长年郁结,猛地惊怒以致痰迷心窍生了心魔。也有可能是以前受过什么刺激,此刻重温噩梦困住心神。王爷不妨试试跟她说说话,兴许下一刻她就醒了。”
沈圆月是神将,打过无数次生死硬仗,世上有几件事能刺激她?
达步陵昊竟轻轻笑了起来,俯□贴在沈圆月耳边说道:“他死了十三年,早已变成枯骨。你替他养大了儿子,替他老母亲送了终,没什么对不起他。你现在是我达步陵昊的女人,快醒来。”
仿佛听到了他的话,睡梦中的沈圆月皱紧了眉头。
见状,唇边的笑意更深:“听到了?那就快醒,我已自作主张娶了你,今夜是我们洞房花烛呐。”
可不管他说什么,沈圆月都闭着眼睛,用沉默应对他的话语。
渐渐的,夜晚很快过去,没多久黄昏又悄然降临。天阴沉沉的,像一块灰蒙蒙的幕布。卧房内寂静无声,连鲜红的纱帐也散发着一层清冷的光彩。达步陵昊支着头侧躺在沈圆月身侧,专注地盯着沈圆月安静的睡颜,仿佛化成了一尊雕像。
欢喜带着几个小厮守在门外,焦虑万分地低声讨论。自从沈圆月昏迷,达步陵昊一口水也没喝,再这样下去需要求医的就不止定北侯一人了。
夜幕再次降临,欢喜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爷。”
“出去。”达步陵昊轻声道。
欢喜鼓起勇气:“爷,沈少爷今天在府外同人打架,脑袋让人打破了。对方的父亲还找上门来,说要找沈将军论理。”
达步陵昊一直在照顾沈圆月,没空管沈开,只得将沈开暂时送到墨卓家中暂住。这才一天,沈开怎么就闯祸了?他坐起身,面无表情地拍了拍沈圆月的手:“我是一家之主,自会照顾好小开不叫他受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