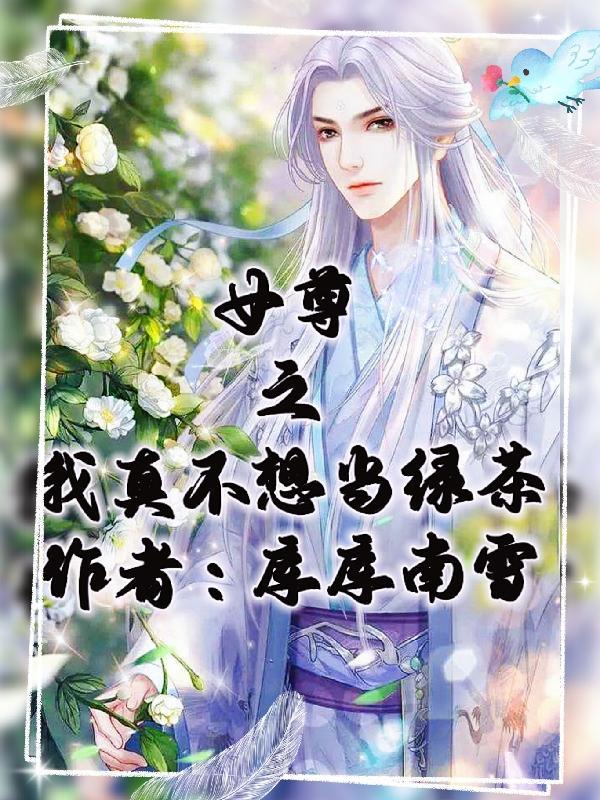极品中文>太阳作者 > 第32章(第1页)
第32章(第1页)
死一般的寂静一下在房间里铺开,他缓了几秒,平息一下情绪,心下打定主意再苦口婆心劝上两句,要还不听就算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但下一秒,宋薄言把手上的医用棉球扔进垃圾桶,镊子丢回医药箱,就像是浑身上下的所有力气都被抽空了一样,陷进了椅子里,声音轻得仿佛只剩一口气。
“是我活该。”
当年的他,确实是自我又愚蠢。
仗着池清霁对他的喜欢,就连出国留学这种事都没有和她商量过,一开始是因为不熟没必要,到后来又怕她知道了舍不得,会动摇他往外走的决心。
那时候他的想法很简单,到了巴尔的摩稳定下来,再好好跟池清霁把话说开,谈谈他们的未来,以及等他回国之后结婚的事情。
他能想到池清霁会生气,会哭,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任打任骂。
但宋薄言毕竟是第一次留学,和旅行,夏令营或是游学都不同,那是真正意义上独自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地他乡生活好几年,所有问题他都需要自己解决。
从下飞机落地开始,一系列想到的想不到的事情全都接踵而至。
等到找到房子,买好生活用品,所有手续告一段落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他总算意识到自己应该和国内取得联系,于是在一个深夜拨通了池清霁的电话。
直到今天,他也忘不掉池清霁当时在电话那头说的话:
“宋薄言,你去国外留学,杨开远他们全都知道,是吗?我以为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只是你的朋友。”
“你从头到尾就是仗着我喜欢你,你就是仗着我离不开你,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不喜欢你了,我不需要你了。”
她就像是一只被全世界背叛,精疲力尽的受伤小狗,早已没有了哭和叫的力气,只有平静下死死压抑的颤抖。
宋薄言甚至插不上一句嘴,没有任何可以为自己解释的立场与对白,只能任由她哑着嗓子用比嚎啕大哭更让人揪心一百倍的语气,为他做出最后的死亡宣判:
“我们分手吧,宋薄言,祝你鹏程似锦。”
直到那一刻,宋薄言才知道他有多么自大,仗着池清霁对他看似毫无底线的喜欢做了多么狂妄而又愚蠢的事情。
也是直到那一刻,宋薄言意识到,这段关系中被需要的从来就不是他,真正离不开的人从来都不是池清霁。
他被挂了电话后就直接订了最近一班的机票,在候机大厅坐了一整夜。
直到清晨,巴尔的摩第一缕阳光穿破云层的时候,宋薄言接到了宋持风的电话。
那一通电话只持续了一分钟不到,但却让宋薄言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都回不过神来——
就在他登上去往异国班机,在与国内失去联系的第二天,池清霁的爸爸,他曾经的恩师,跳楼自杀了。
深渊(一)
每年清明,宋薄言不管再忙,都会回一趟庆城,给母亲扫墓。
麓城的四月还带着凉气,入了夜依旧森冷,但庆城的四月却已是春暖花开,阳光宜人。
宋老爷子过年都没把二子盼回来,满打满算小一年没见他,这次听说他要回来,是真的乐得合不拢嘴,光是团圆家宴的菜谱就跟陈管家写了足足三个版本。
“是狮子头呢,还是东坡肉呢……”
“我觉得狮子头可能好点,他不太喜欢油腻。”
“行那就狮子头!”
宋薄言被司机接回宋家老宅,比预计的时间要早上小二十分钟。
他拎着行李箱推门进去就看他爸和陈管家两颗中年男人头凑在一起讨论菜单,虽然讨论的话题很绿色健康,但画面总归是不怎么养眼。
宋薄言一秒都不带犹豫的从两个人背后路过,就连扬起的风都格外清淡。
小辈房间都在二楼,宋薄言熟稔上了楼梯,抬眼正好撞见宋持风从书房出来,眉眼凝着股暗色,看起来心情不太好的样子。
一对心情不佳的兄弟在自家楼梯上相遇,片刻对视后,宋持风侧了侧身示意让他先走,宋薄言却没动:“我找你有事。”
两人就近进了书房,宋薄言先把行李箱放在了书房门口,不等宋持风坐下便直接开口:“池清霁走的那年,你说你帮我找她。”
在池清霁消失后,宋薄言失魂落魄没日没夜地找了好几天,所有她可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一遍,最后只能确定,她可能已经不在庆城。
可谁都知道,搜索范围一旦扩大到全国,那寻找的时间可能就不能以天,而是要以年为单位。
当时jhu已经开学,宋持风就劝他说:“你先回去读书,人我帮你找。”
兄弟俩只相差两岁,宋持风那年也就大二在读,谈吐投足间却已经有十足的长兄风采,这么大的一句话说出来不光不显得空,还带着股言出必行的气势。
后来他回了巴尔的摩,不时地便会打电话回国,在一次一次的失望中从来没有怀疑过宋持风给他的交代。
“你真的找了吗?”
直到上次他在刘姐口中得知,池清霁是麓城大学新闻系毕业的。
麓城大学,就是当年他们一起商量着填的志愿。
比起全国地毯式的搜寻,从行为逻辑上先进行推理显然是更高效的方式。
宋薄言不相信宋持风会想不到。
“找了。”
闻言,宋持风回过头来看着他,一双眼睛里却没有半点虚愧之色。
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藏又能藏到哪里去,她高考成绩那么理想,不可能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