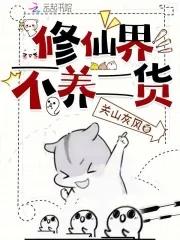极品中文>恶汉眼里的小桃花 > 第二十七章 走马震金城一求推荐收藏(第2页)
第二十七章 走马震金城一求推荐收藏(第2页)
();() 西北苦寒,到了冬季往往会出现粮草不济的情况。
所以这一次回来,董玉特地买了不少的粮草,以防寒冬时节粮草出现紧缺。随行的还有几十车的松油,加起来足有几百坛子。董俷随车队走了这么久,自然清楚车上都是什么。
把粮草堆起来,泼上了松油。
一时间,整个营寨就成了一片火海。人喊马嘶,乱成一团。那些冲进营帐的人发现,所有的营帐里都堆放着粮草,火一起,在营帐里的那些官兵顿时陷入火海。
轰的一声,在中军大帐里拜访的松油坛子受不住热,炸开了。
破碎的瓦片一下子成了勾魂贴。随北宫玉冲进大帐里的几十名官兵被炸得是支离破碎。连带着在营帐外面的马,也被大火惊的唏溜溜暴叫,四处的乱跑起来。
北宫玉满身血污,狼狈不堪的冲出了大帐。
他翻身上马,大声叫喊道:“中计了,我们中计了,快冲出营寨!”
马玩和杨秋正拼命的安抚胯下的坐骑,听到北宫玉的喊叫声,马玩勃然大怒,“二弟,你不是说都安排好了吗?”
“我那知道那小畜生如此狡猾?”
杨秋抓住马玩的胳膊,“阳石,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快点一起杀出去。”
话音未落,只听一声野马暴嘶,声如沉雷。所有的马匹又是一阵惊慌,董召和裴元绍各带了五十人从营寨两边杀出。虽只有百人,却杀气冲天。那董召和裴元绍虽然不算出众,可那也要看和谁比较。和董俷不行,但是和马玩两人,却不分伯仲。
“贼将休走,裴元绍在此!”
裴元绍一颤手中大枪,扑棱棱抖出十几个枪花。马玩正手忙脚乱的安抚坐骑,哪晓得裴元绍二话不说就冲过来。手中镔铁枪想要封挡,却不想战马已经失控,一个蹶子就把他给摔下马来。马玩被摔得晕头转向,盔歪甲斜。大枪也不知扔到哪儿去了,站起来后还有点发懵。裴元绍已经过来,大枪噗的一声把马玩穿了一个透心。
与此同时,那董召和杨秋也站在一起。
一个是惊慌失措,一个却是以逸待劳。两人本来就不分上下,如今却高下分明。
三个回合,杨秋被董召一刀砍去了头盔。
吓得他拨马就走,哪知道刚躲过一头狼,迎面就碰到了一头老虎。董俷跨坐斑点兽,大锤上下翻飞。那可真的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从营寨门口一路杀过来,不晓得有多少人死在了他的垂下。大锤上沾着粘稠的鲜血,董俷的身上还有不少黄白脑浆。整个人好像一尊煞神,所过之处,但见一片血雨腥风,好凄惨。
杨秋不认识董俷,心一横,手中大枪分心便刺。
他可是听说了,那员猛将兄是用一把奇形的大刀,可不是用双锤。如果他知道董俷真正的武器不是刀而是锤的话,那打死他都不会和董俷跑过来过招。那不是过招,根本是送死。
董俷冷笑一声,左手锤抬起向大枪一磕,铛的一声,杨秋手的枪就飞了。
双手鲜血淋漓,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董俷已经和他错马而过。在错马的一刹那,董俷右手锤突然反手抡起,这叫做回身望月。蓬的把杨秋的护背旗砸的粉碎。
那杨秋在马上口吐鲜血,一头栽倒在地上。
临死之前,这家伙扔在疑惑:“不是说那员猛将用的是刀?究竟有几个猛将啊!”
别看官兵人多,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无心在抵抗。
随着马玩和杨秋毙命,官兵们立刻就炸了锅,“不好了,都尉都死了,快跑啊!”
可营寨就那么小,营门口有绿漪带着尚能活动的一百个羌兵,弯弓搭箭。
北宫玉在溃兵的簇拥下朝营门口蹭。绿漪眼睛尖,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的北宫。
“奸贼,休走!”
绿漪拍马舞枪就冲向了北宫玉。那北宫玉也怒了,老子输给男人也就罢了,你一个小姑娘家也过来欺负我?中原有句老话,叫做士可忍庶不可忍,拼了吧。
他舞刀迎向绿漪,大刀翻飞,片片寒光。
绿漪也抖擞精神,使出了看家的本领。不要求战败他,只求能拖住他一会儿,等公子过来。
可那北宫玉毕竟是纵横西北多年的人物,刀马之精湛,也非俗人可比。
绿漪的枪法不错,却挡不住北宫玉的拼命砍杀。几个回合下来,就累得气喘吁吁,香汗淋漓。
一个不留神,绿漪的大枪被刀磕中。
她才多大的力气,和普通女人比起来是厉害,但是在北宫玉面前,还小了些。
手一麻,大枪咻的就飞了出去。
北宫玉红着眼睛挥刀就砍,而绿漪却已经没有还手的力气。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董俷在远处一声雷吼:“北宫玉,尔敢伤绿漪,誓取汝命!”
这一嗓子,好像惊雷一样。
那胯下的马唏溜溜长嘶,立刻就直起了身子。几乎是在同时,一道乌芒破空出现。
砰的穿透了北宫玉的肩膀。
北宫玉可是披着一套价值五十万钱的上好盔甲,却挡不住这一击。
盔甲破碎,北宫玉惨叫一声从马上跌下来。有亲兵立刻上前,护着北宫玉就走。
();() 他们也不敢会金城了,朝着远处就跑。
董俷见一枪没能要了北宫玉的性命,这心头的火气更大。舞锤追过来,奈何这溃兵太多了,堪堪挡住了他的路。等他杀过去的时候,北宫玉已经跑的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