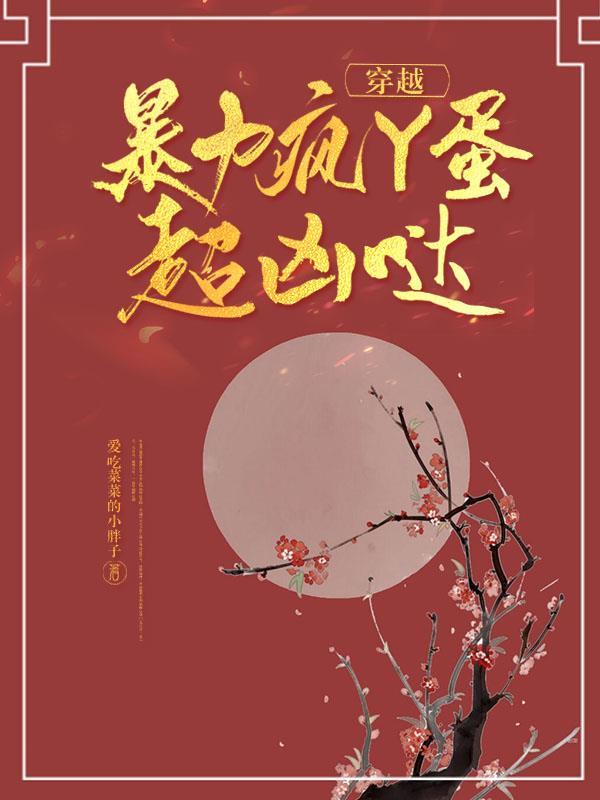极品中文>朱火成简介 > 第4頁(第1页)
第4頁(第1页)
燭火照舊無風自跳。
秦雪若長嘆一口氣,坐了大半夜,雙腿麻得快無知無覺,緩緩而立,點了三支香,又對著案上供奉的禹應煥血跡斑斑的甲冑與佩劍拜了又拜。
「未婚夫……啊現在成了禮,應該喚你夫君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呢因為不想嫁人受束縛,確實是為了你噩耗歡喜過一場,咳,不知者無罪嗎,我也不知道你過得這麼苦,所以你要是變成厲鬼索命,可千萬別來索我的命。唉你爹忒沒良心了,不像話,不過沒事,你的身後之事,我們水鏡族會為你撐得風風光光的哈……」
秦雪若邊拜邊碎碎念。
她從來沒有和死人單獨共處一室過。
心內還殘存著些許驚慌害怕。
羅里吧嗦講了一堆的重點是,禹應煥的鬼魂千萬別來折騰她。
三拜完畢,秦雪若正欲起身,忽得脖子一僵,凝在案前。
眼光餘光一會兒移到甲冑上,一會兒暗瞥著棺槨。
甲冑透著腥氣兒,也不知染了多少人的血。
不對。
甲冑不對勁。
她守前半夜時無聊得緊,將帳內陳設一處一處地瞧了又瞧,紋飾圖案類的也記在心上,聊作打發時間捱過漫漫長夜之用。
連繡鞋上有幾朵花都摸了一遍。
禹應煥頭盔上的紅纓,明明是朝著東邊,在她和辛乙、百里赫閒聊完回來之後,又朝向西邊去了。
必是有人趁著這個空當做了手腳!
或是在翻找些什麼。
此前的指甲劃棺木,也許是有人故意製造的聲響,拿定了她一個女兒家會害怕離開,為他行不軌之事提供時機,一招調虎離山之計。
帳口有人時時把守未離寸步,若有旁人做些動作……便可能是與她一起同處內室!
帳???內空曠得很,唯一能藏人的地方,便是……便是……
秦雪若的後背頓時竄起一片細密的冷汗,動物的本能告訴她已被捲入一場不明的危機之中。
她站直了身子,隨即暴起拔出祭供著的禹應煥的佩劍,轉身疾言厲色,一劍劈向棺木一角,暴喝道:
「大膽!何人敢在此處裝神弄鬼!」
她這未婚亡夫的佩劍大有來頭,是三年前軍中比武魁的彩頭,珨王親賜,名為「純闕」,削鐵如泥,吹毛斷髮。禹應煥的棺木為百年梓木所制,堅厚無比,一劍下去,入木三分。
秦雪若不通武藝,完全是下意識的反應,光憑蠻力劈砍,以至於劍鋒嵌入棺材邊角,秦雪若再想收力之時,劍還拔不出來了。
糟了。
其實這一劍下去她便後悔了,悔不該打草驚蛇。
無論埋伏在此的人是誰,是哪方勢力派來的,都只是趁她出帳時進行翻找,明顯來者也不想驚動了誰。
她若不聲張,尋個藉口再出去避一避,這一茬便平平穩穩地過去了,發生了什麼都不與她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