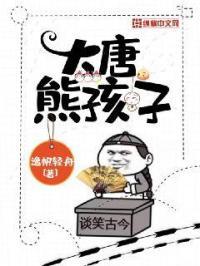极品中文>穿越夫郎有点甜by羽春TXT > 第23頁(第1页)
第23頁(第1页)
這事畢竟要去跟頭頂的小老大講一聲,白謹還是知道自己緊要在意的人是誰。
院子裡格外的安靜,劉先生居然還沒開始講課,難道是只布置了功課讓他們完成嗎?
沒聽到之乎者也以及劉先生慢慢用故事敘述含義,白謹略微有些詫異。
等他一跨進房內,就發現了不對勁——
小廝正跪在地上,戰戰兢兢地哭訴著什麼,他語過快,聲調淒涼,白謹一時間沒聽清對方在說什麼。
劉先生老神在在地坐在一旁,事不關己地喝著茶,手裡正捧著《尚書》讀。
劉善正坐書桌旁寫功課,像屁股下有釘子一樣坐立不安,時不時地朝小廝這好奇地望來一眼,被劉先生警告地看了一眼後才有所收斂。
白謹被這奇怪的一幕弄得緊張不已。
「白謹,他說你娘親故意收買門房,偷奸耍滑躲懶去了,是真的嗎?」左安禮語氣中調侃多過質問,彎眸微笑的模樣讓白謹淺淺地放下心。
要是左安禮真信了這套說辭,小廝也不可能跪在這鬼吼鬼叫了。
「當然不是,我第一次上工,娘親不放心我,特地趕在中午來見我一面,不是很正常的事嗎?」白謹一臉無辜,他想破頭也不明白為什么小廝會用這樣拙劣的謊言來對付自己。
小廝顯然相當不服,氣惱地說:「馬夫說看見你娘給門房塞東西了!況且才一旬不到就請假,你這樣的人會認真做少爺交代的事嗎?!」
他其實也不是自己一拍腦袋就想出這麼個計謀來,而是有跡可循。
縣丞家公子的書童就是被這般擠兌走的,只需要三言兩語挑撥給主人家就輕輕鬆鬆搞定一個人。
不是很重要的崗位,就算書童沒做錯,但經過添油加醋,主人家心裡也會不舒服,寧願換個人也不想讓他們「尸位素餐」。
可惜他遇見的是經歷過烏煙瘴氣世家爭鬥的左安禮,對這點小手段簡直看不上眼。就算是拿到左夫人那裡說理,他們更厭惡的還是愛挑撥離間的下人。
白謹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
話說,這是吧?!
對了,這肯定就是宅斗!
他居然也經歷了電視劇里才有的宅斗劇情!!
剛才的忐忑不安在此刻全都化為烏有,白謹隱隱還有些激動興奮。
左安禮不太理解旁邊的小書童怎麼忽然情緒激昂起來,他平靜地說:「哦,是嗎?他不認真,難道你就很負責了麼?」
小廝見左安禮年紀小,只以為方才對方讓他跪下是因為他衝撞了看重的書童,丟了面子,完全沒想過其他。
這會兒神色和緩了,肯定是被他哄騙了過去,便諂媚討好地說:「只要是少爺吩咐的事情,小的上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辭。」
他之所以擺明了嫉妒白謹,就是因為自己也讀過書,咬文嚼字不在話下,最後卻只能成為一個跑腿的小廝,這讓他怎麼可能甘心!
左安禮眼睛流露出諷刺:「本事不大,野心不小。心氣如此高,我這留不下你。」
小廝臉色驟變,不清楚自己是哪招惹到了這位小少爺,倉惶求饒:「小少爺,您在說什麼?小的哪裡做錯了?小的再也不敢了,就不必……麻煩夫人了吧。」
左安禮神情微冷,不欲多做糾纏,直接叫護衛進來將人給帶走了。
心比天高的下人是用不得的,將他交給娘親就行。
他又恢復了溫和清雅的模樣,半點看不出剛才的凜然氣勢,拱手道:「讓先生見笑了。」
劉先生擺擺手,「無礙,你處理得很好。」
白謹看得目瞪口呆。
卻不想突然被劉先生抽中提問:「白謹,你從這件事看出了什麼?」
白謹倏地被點名,磕磕巴巴地說:「身處高位,總、總是會被人嫉妒、陷害?」
劉善噗嗤一笑,左安禮嘴角上揚,溫柔地沒笑出聲來。
白謹尷尬地撓了撓臉蛋。
結果下一個遭殃的就是出聲的劉善,劉先生對他可就沒這麼客氣了,「劉善,你來說說。」
剛剛還幸災樂禍的劉善瞬間苦了臉:「我覺得吧,白謹做事應該警惕點兒,不應該隨便就被人抓住把柄。比如這次請假,你怎麼還讓一個討厭你的人來幫你呢,這不是趕著讓人陷害嗎?」
白謹詫異道:「我是讓門房來跟少爺說的。」
劉善比他還震驚:「是嗎?」
劉先生哭笑不得地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真正想要害你的人,千方百計都會找出謀害你的方法。為師要跟你們講的這一課,是在為人處世上……」
白謹不敢打斷劉先生的講課,只是他還有要事要辦,一時間如坐針氈。
左安禮眼角瞥見白謹額頭上冒出的細密汗珠,輕咳了一聲,適時斷在了劉先生停頓之際。
他目光清澄地對劉先生說:「先生,抱歉。學生想起來有要事還要去找我娘親,能否讓學生請個假呢?」
劉先生本來就是縣令家給左安禮單獨請的夫子,要教導的其實只有他一人,自然無有不應。
左安禮自然而然地拉著白謹出來,笑吟吟地開口:「說吧,發生什麼事了?我看剛才就跟有針扎你似的,眼睛也到處亂瞟。」
白謹不好意思地紅了臉,嘴甜地說:「少爺果然耳聰目明,在下甘拜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