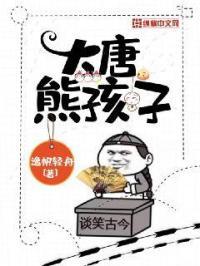极品中文>乱世凰歌86集免费观看 > 第三十三章 连赢九次(第1页)
第三十三章 连赢九次(第1页)
那便是骰子中注入了铁,而且不是均匀的,倾向于小的那一半,因此小的点数触碰盅壁时,声音会更沉重,相反则更轻巧。
桌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磁石,平时无人会觉,但已足够吸引骰子,只要摇得幅度大力量小,必定是大的点数在上。
因此樊塬必须摇得十分费劲,才能避免磁石吸引小的那一半。
这也是金玉坊能稳赚不赔的原因。
若赌坊不想要大,就会启动桌下的机关,直接将骰子翻身,得到小。
这是她仅有七八岁时误入金玉坊,便看出的端倪。
因为这个,某个金袋子许她在金家旗下所有商铺买东西不用花钱,只要她不进赌坊半步。
“哈哈哈哈……好多钱啊!”于显民捧着一堆金银财宝流哈喇子,整个人都快幸福得飘起来了。
于芷桐给了他一个白眼,抱怨道:“好无聊啊,我想回府了。”
“回去吧回去吧。”于显民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满脸堆笑得望着虞稚,“安歌妹妹,咱们继续赌吗?”
虞稚平静地与樊塬对视,气定神闲地启唇:“继续,大。”
“哼!我偏不回去!”于芷桐瞪了瞪杏眼,随手抓了一把银钱,快环顾四周,去玩儿斗蛐蛐去了。
樊塬深呼吸一口气,在众人地注目下再次摇起了骰盅。
这一次,他的注意力不在骰盅上,而是一瞬不瞬地凝视虞稚,誓要看出端倪。
再好的运气,骰子也不会三番四次都是大,她绝对动了手脚,只是在场所有人都未察觉。
然而,整个摇骰子的过程中,她都没有动半分,连头丝都不曾被风吹起。
“大大大!天啊又是大!”
直到哄闹声再次在耳畔响起,樊塬才回过神来,呆滞地盯着台面上的骰子,扫过皆为大的点数,手臂僵在空中。
一共赌了九次,没有一次失手,虞稚赚得盆满钵满,怕是下次再来,金玉坊就得赶她走了。
最后虞稚觉得无趣了,便叫一个小厮抬了金银送去于府,与于显民于芷桐一道出了金玉坊。
樊塬望着虞稚离去的背影,自他被冠上赌神之名后,第一次感受到了挫败之感。
“樊管事,这个姑娘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耳畔响起苍老的声音,樊塬回头,原来是一位金玉坊的老伙计,在金玉坊做了大半辈子了,十分受尊重。
他微蹙眉心:“什么人?”
这样变态的人世上还有第二个?
“大约十年前……金家第一座赌坊开设于九重江之上,五州交汇的不夜华廊,正是名声鹊起时,来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老者娓娓道来,“就如这位姑娘一样,连赢九次,次次压大,赔了金玉坊不少钱。”
“七八岁……?”樊塬咬着这三个字,仿佛在听一个可怕的笑话,接着问,“那她的事迹为何没有传扬出去?”
如果传扬了出去,可就没有他这个赌神了。
“因为这个小女孩后来与坊主见了一面,尽数归还所赢金银,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坊主也叮嘱我们保守秘密,故此知道的人不多。”老者抬眼望着他,“我说这些是觉得……这位于小姐是否正是当年那个小女孩,是否要禀报坊主?”
樊塬慎重地颔:“要。”
不禀报坊主,不得赔钱赔得他棺材本都没有了?
另一边。
三人出了金玉坊,在酒楼吃了午饭,时辰尚早,于芷桐非要去逛街买东西,以消她心头之恨。
于是,成衣店,饰居,胭脂阁被她逛了个遍,还“好心好意”的给虞稚买了一堆黑胭脂,于显民提都提不动了,只好找个车夫先送回府去。
于显民啧啧嘴,阴阳怪气地说:“这以后谁敢娶你啊,有金山银山也得被你败光咯。”
“要你管,又没让你娶!”于芷桐翻着白眼,用屁股顶开他,继续挑选饰去了,如捡大白菜般不停要求包起来,把小二乐得找不着北。
反观虞稚却半个饰物也没买,目光扫过眼花缭乱的金银珠钗,波澜不惊,毫无兴趣。
对她而言,买珠钗就是浪费钱,给她一些金银铜铁,分分钟幻化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钗步摇。
只是金银易得,却柔软无力,她更需要大量的铁……
旁边的于显民突然拿起一只玉簪,在虞稚的头上比划:“好妹妹,这玉簪好生衬你啊,显得你更加肌肤如雪了,买下它吧!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嘛,如花似玉的年纪怎么能不好好打扮呢!”38ooxs38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