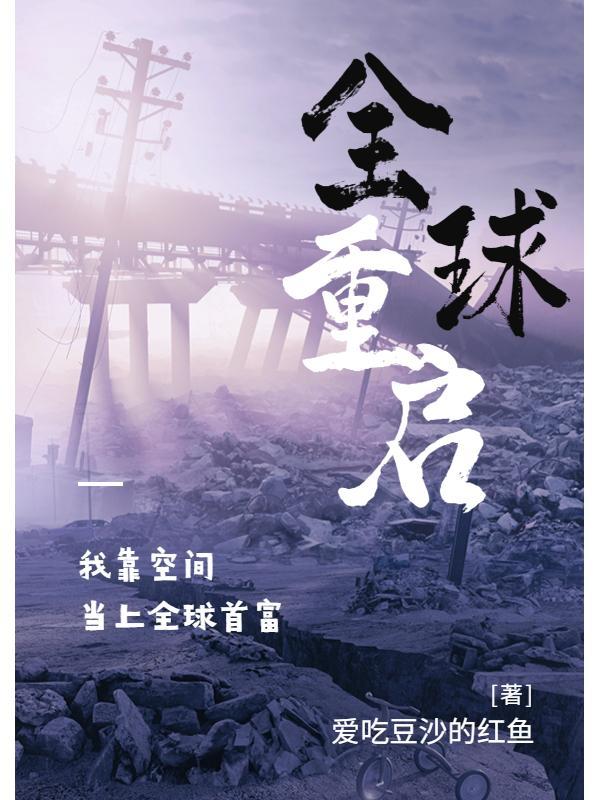极品中文>假千金卡皮吧啦在种田综艺爆红了[穿书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
“你如果不愿意的话,这婚就当没结过,反正没领证呢。”
“阿姨收你做干女儿,你如果愿意的话,只管拿我当妈妈看。”
李连枝笑得很温柔,牵着纪屯的手也软软的,垂着眼看她的样子,符合纪屯对一个母亲所有的想象。
心里头有一根弦“噔”一下响了一声,纪屯心被扯着有些难受,这种感觉好像是等待了很久的委屈,来得莫名其妙。
明明她不是原主,她对母爱是没有执念的——应该是没有的。
女人头顶的灯光像是从她身上照出来的辉光,不知是不是太刺眼,纪屯低下了头。
李连枝揽过她毛茸茸的脑袋,按到胸口搓一搓,轻声道:“你要真是我女儿就好了,我做梦都会笑醒。”
“有些人不懂得珍惜的,自然有人会珍惜。”
纪屯咽了下口水,觉得原主的意识在自己心里没散干净,不然为什么此刻心中有些不适,酸酸的,让她想要揉一揉。
纪屯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点了头,晕乎乎跟着人走。
睡了五个多月,哪怕每天有安排肌肉按摩,容叙身上的肌肉也不可避免的有些萎缩,好在时间并不是很长,并不算太严重。
容叙在护工的搀扶下站起来,能看得出腿脚使不上力,撑在栏杆上喘着气,头上冒出一层薄汗,唇色也苍白的可怕。
护工是个很有力量的中年男性,他托举的力道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人站不稳摔下去,也能够让他最大程度地靠自己站起来。
第一天的复健是非常艰难的,纪屯觉得自己身为一个外人,不应该去看他这么狼狈的模样,找了个理由溜了出去。
两个小时过去,容叙汗如雨下,病号服后背已经被浸湿了,好在运动下来面色红润,看起来精神不错。
李连枝见他换好衣物,将容淇容泽找了个理由赶出去,坐在凳子上静静看着容叙擦汗。
“妈有话对我说?”容叙将毛巾一丝不茍迭好,放到轮椅的扶手上。
“有。”
容叙滚动轮椅的滚轮,调了个方向对着她,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小屯的事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想怎么解决?”
容叙眼皮垂下去,“我有数。”
“你有数个屁,我知道你是最讨厌受人摆布的主,这事也是我糊涂了,当时怎么就由着你爸胡来给答应下来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不愿意,你。。。。。。”
容叙忽然打断:“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
李连枝都要笑了,这个儿子她最清楚,从小就深沉得很,情绪也不外露,无论高兴了生气了憋屈了都只是笑,越气笑得越开心,表面上看不出,心里的盘算却比谁都要多,她作为他的母亲都很难拿准他的态度。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最厌恶被人支配,感情也最为冷淡,这桩强加给他的婚事他不可能会高兴。
“你最轴,你认定的事根本不可能改变。”
容叙轻轻一笑,“对,不可能改变。”
“所以我也不逼你,你就当这事没发生过,我正好一直想收她做干女儿,以后就当是你们亲妹妹,她愿意怎么过都随她高兴。”李连枝轻舒一口气。
男人指尖一下一下打着大腿,意味不明地笑着,“妈,你没懂我意思。”
“什么意思?”
“我有数,你不要插手。”
李连枝都要气笑了,“还能是你喜欢她不成?”
看着男人不置可否浅勾着的唇,李连枝渐渐眯起眼睛,上下打量他,“你是不是被人夺舍了?”
这跟她印象里的儿子不一样,她猜过很多种可能,唯独没猜到他是这个态度。
“没有,母亲。”
他很少会叫李连枝母亲,母亲这个叫法往往是带这些庄重的,李连枝也不由正色,淡着神色听他讲。
就见容叙神情里带这些难言的轻松,好像在回忆美好往事,娓娓道来:“在我成为植物人的那些天,我一直能听到外界的声音,只是动不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没有听见一点声音,你知道,这是能把人逼疯的安静。”
李连枝瞪大眼睛,听到他继续不急不缓说着:“她陪我说了很多话,带着我去晒太阳,用心经营我们的园子,带着我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地散步,晒太阳,唱歌,或者是自言自语。”
“在我醒来的前几天,我只能听到她的声音,感觉到她的触碰,听不见其他人的声音,更无法回应,这很奇妙。”
“我原本以为,我只是喜欢一个热闹,有人声的环境,但你知道,我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这也是他想了许久才想出来的结论,很奇妙,说不上来为什么,也许只是因为那个人是她。
他从来都不喜欢热闹喧嚣,哪怕在成为植物人之后,想要听一听声音,但在醒来之后,他依然是一个享受孤独的人。
他依然讨厌喧闹的人群,无谓的对话,只唯独喜欢上了她在自己身边叽叽喳喳的样子。
甚至比在昏迷的时候更渴望听到她的声音,她很矛盾,在人前会将所有的情绪掩下,很少说话,人后却能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好似做回了自己。
像一只胆小缩在壳里的乌龟,要很小心,才能哄着多说些话,多表露一些情绪。
容叙很少说这么长一段话,更没如此剖心过,李连枝眼睫颤动着,张了张嘴。
半晌,她轻声说:“那如果,是她不喜欢你,她想要离婚呢?”
此话一出,容叙表情有一刻空白,两人对视着,半天都没有人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