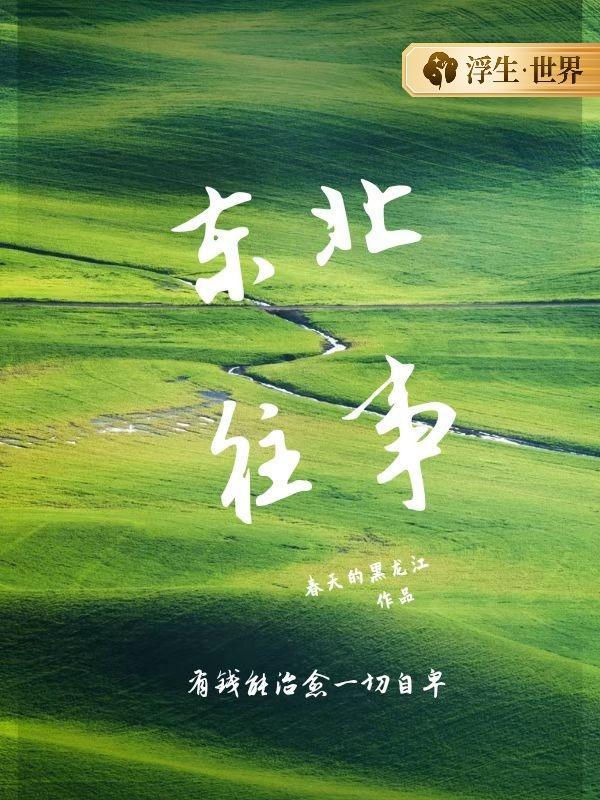极品中文>hp德哈文完结 > 第99章(第1页)
第99章(第1页)
德拉科已经睡醒了。他身处一片漆黑当中,仍然半躺在床上,也不愿意点灯。哈利静静地走进屋子,把剩下的包裹放在床头柜上拆开,里面是一捆蜡烛,还有一个火柴盒。
“我去镇上买了一些,”他擦了一根火柴,“苏伦妈妈说屋子里没有蜡烛。”
屋子亮了起来。哈利握着蜡烛,把它和原先的牛油烛交换了位置,放稳在桌面上。接着,他像昨天一样坐在床边,又从裤兜里掏出杂货商找的铜币,一枚枚数着。
“那个商人说,十枚铜币是一枚银币,一百枚银币换一枚金币”哈利拿起一枚铜币观察——这钱币和英国的便士看上去十分相像,只不过图案换成了城堡。他花了极长的时间数币,似乎只是在避免和德拉科对视。
“我问了几个人,没有什么人知道金苹果是什么这里的人很好,苏伦妈妈说我们可以呆在这里,只向我们收了一些伙食钱还有就是,我在沙滩上遇见了那对卖花母子,我说,他们应该感谢的是你——”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哈利的手停住了。他转头望向德拉科,那双眼睛的颜色明明很浅,却深不见底。
“我以为……你会想要知道。”哈利不由放低了声音,“我们是一起的,不是吗?”
德拉科再次沉默。
蜡烛的味道比牛油烛好闻许多,也更加明亮。哈利收起了钱币,注视着火光摇曳。
许久,德拉科又开了口:“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扔下那个男孩不管?”
“我”哈利顿了一下,“我就是知道。”
而这是真话。
从小男孩从船舱跑出来的那刻,他就知道。连他自己都不清楚这是哪里来的肯定。德拉科没有再说话,哈利看了一看他腿上新缠的纱布,问:“感觉怎么样?”
“还行。”
这不一定是真话。
如果梦里的德拉科和现实中的那个在应对事情的态度上相差不太多的话——目前来讲大概是这样的——那么他也一定是个很怕疼的人。哈利至今还记得开学时在书店门前听到的惨叫。但德拉科现在却没有叫痛,唯一的抱怨只是关于屋里的味道。
也许,哈利猜想,是因为真的疼了。就像那个嚣张跋扈的马尔福只有在人前吃亏时,才会闭口不言。
苏伦妈妈在门外大喊,说晚餐已经做好。哈利把火柴盒放在床头柜上,起身准备离开。“我去把吃的给你拿过来。”他说。
“不用了,我不饿。”德拉科摇摇头。哈利朝他看一眼,随后点点头,走时带上了房门。
密闭的房间里鼓胀着燃蜡的味道,德拉科注视着木门合上,门缝关严,缓缓吐出一口气。他闭上眼睛,咬住自己的下唇,尝试性地挪动右腿。
疼痛顺着每一根神经传递到大脑。
该死的。
他立刻停止了动作,以防自己残废。
半天下来,腿上的伤已经没有昨天那么难耐。谢天谢地,最艰难的时间是夜晚,而他那个时候意识正在圣戈萨赫罗的球场上奔跑。但当他在这个小茅屋里一睁开眼,痛感便毫不留情地涌回到身体,伙同着外伤愈合带来的瘙痒,令他不得不一秒清醒,并清楚记起自己在梦里的处境。
如果不是那个小男孩,不是波特临时走开,他就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理论上,他应该把那个好管闲事的罪魁祸首骂一顿,甚至是想方设法害他一害。但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很生气。
准确来讲,是一点也不生气。
相反的,他感到一股异样的情绪在体内弥漫。它同愤怒一样,叫人坐立不安、不受控制,却让人舒服,甚至让人想要靠近——如同牛油与蜡,燃起的火苗同样有温度,却是两种东西。
德拉科偏过头,看向床头柜上的蜡烛。烛泪又滴了许多,底部垫着的银盘上堆起泛白的蜡块。时间分分秒秒过去,蜡烛也越来越短,德拉科终于发现,他在等待。
等待。
这是他这一整天做的唯一一件事情。
波特大概以为他在睡觉,德拉科想。早些时候,他闭着眼睛休息,听见轻轻的开门声,只一会儿,又尽可能小声地关上。从那之后,他便再也没合上过眼睛。
他想翻身,却不被允许;想喝水,又不愿也没力气隔着门朝陌生人嚷嚷。更多的,他想知道哈利去了哪里,在干什么,会在什么时候回来。令人恼火的是,这人偏偏去了一整天,像是完全忘记了这里还有个名叫德拉科·马尔福的人。
可能受了伤的人格外脆弱,也可能是密闭的屋子让人感到害怕,总之,德拉科很快后悔自己拒绝了晚饭,即使确实一点不饿……
“德拉科?”
突然,哈利从门外探进个头来。德拉科抬起头看到他,表情凝固。黑发男孩手里端着一个杯子,走到床边,简短地说:“万一你渴了。”
他将杯子放在柜子上,没有多逗留。
又是接骨木花茶。
德拉科捧着瓷杯,热气模糊了视线。没有了牛油烛焦味的打扰,他才留意到这种茶有股独特的清香,闻起来像清晨的森林。
茶汤是淡淡的浅黄色,上面飘着接骨木花。他注视着那白色的小花朵,轻声念道:“哈利……”
他瞥了一眼房门。
在梦里,他们从来都是称呼彼此的名字,到现在也有两个月了。即使这样,德拉科仍然有意无意地避免直接这么叫。或许这两个音节对他来说太惊心动魄,像是那个禁言魔咒一样,总是堵住嗓子。所以他念得很小声,仿佛再用力一些,就会梗在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