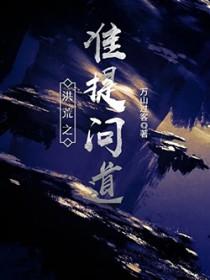极品中文>我有一个愿望阅读理解答案 > 第十四章 对话(第2页)
第十四章 对话(第2页)
也就如今与自身有些关系,才从正观那里了解了一些。
贺朝国祚已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前期雄视天下,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官场腐败横生,加之藩镇割据,已有了江河日下的亡国气象。
如今天灾人祸不断,每年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战火虽然没有烧到清净寺所在的州府,百姓面对的苛捐杂税却一日重过一日。
按说这种困苦之时,也正是寺庙搜刮民脂民膏、敛财收地的好机会。
偏偏清净寺地处深山,且庙破人少,对比于其他大寺庙或道观,就毫无竞争力了。
据正空所说,除了山下小河村有个女施主常来上香,他这两年就没怎么看过长头的……
-----------------
禅房中,正观将搭在印善腕上的手抽回来,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师父的内伤已渐渐平稳。”说着,取了桌上的药碗,双手递过去,等他接了,才又说:“服了这剂,虎狼之药便不适用,弟子明日给您换个方子继续温养,相信很快便可好转。”
印善皱着鼻子将汤药一饮而尽,感慨道:“为师本以为自己时日无多,却硬是叫你几副汤药拽了回来,这等妙手回春的手段,不愧是……”可话到这里硬是停住,再不言语。
正观眉眼平和,似对师父的话毫无反应,只是接空碗的手顿了一顿,然后又将盛放清水的碗送到师父面前,温和地说:“弟子的药哪称得上厉害?是师父身体强健的缘故。”
印善闻言,也很快调整了面部表情,只叹道:“可惜为师经此一难根基已坏,今后只能苟延残喘了。”
正观垂眸:“师父奔波多年,正该歇一歇,况且还有弟子在呢。”他边说着,边将两个空碗摞在一起,顺手把窗边的书册梳理齐整,最后推着油灯到桌面正中央,不禁满足地呼出口气。
正要再说话,可低头时突然瞥见地面,不禁皱起了眉,弯腰将老和尚脱下的芒鞋对齐摆放在床边,才又道:“寺门已修好了,小师弟也听话,师父放心便是。”
老和尚原本一直用无奈地眼神看他,听后也是点头,可停顿片刻,突然又问:“他呢?”
正观自然清楚师父嘴里的“他”指的是谁,用比较轻松的口吻笑道:“出身优渥,话不多,人却老实,只有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哦?”印善挑眉:“你也出身尊贵,比之当初的你又如何?”
“当然比弟子那时强得多。”正观莞尔,促狭道:“并未将蔬菜当杂草除了去。”
“还有么?”印善扯动嘴角,下一刻便笑容收敛,表情渐渐严肃的继续追问。
正观微微一愣,半晌后反问:“师父仍不放心?”
印善哼了声:“此人经文不通,行事毫无佛门弟子风范,加之一身白衣,来得又太巧,不得不防啊。”接着又补了句:“师父宗义,徒弟法号竟是宗言,这般胡闹,更不似中原路数。”
“或许他真不是中原人,但……”正观对此却不以为意,合十道:“敢穿白衣,不是俗人便是菩萨。”
“你觉得他是俗人还是菩萨?”印善冷冷地盯着他:“就不能是妖孽?”
“师父别再考弟子了,若您真觉得宗言有问题,又怎会留人住在寺里?”正观苦笑。
“那是老衲身疲力竭,拿人家没办法。”印善嘴硬道。
正观无奈:“当日情形,他明显与杀手并不相识,那刀换了我,绝对躲不过。”顿了顿,他又叹道:“宗言年纪轻轻,又刚入门,有些出格不奇怪,至于何种出身又有什么干系,起码人是好的。”
“此人好坏与我无关,反正都是你的责任,事关性命,你最好在意些!”老和尚也叹了口气。
“弟子心里清楚,这便去准备斋饭了!”正观则不慌不忙地欠身施了一礼,端着托盘便走出禅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