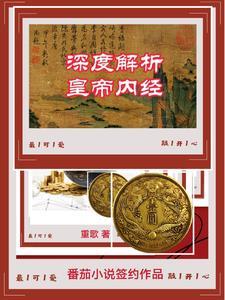极品中文>心上雀 书单晋江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在这里?”季知书还没有反应过来。
“嗯。”时庚原本紧绷的思绪都放松了一些,十分诚恳地说:“只要你愿意,哪里都可以,不会的,我也可以学。”
“把阿姨支开就好了,不会有人打扰。”
季知书想笑又笑不出,只是反问一句:“那,时先生是不是应该把房子里的一些监控给拆了?”
“我可没有录像的习惯。”
时庚肉眼可见地一愣,脸上闪过片刻地慌乱,但是他仍然可以保持极强的镇定。
他惊讶于季知书的观察力:“你都知道多少?”
“除了摄像头,定位器,还有什么?”季知书不羞不恼,反而用着亲昵的语气问,“时先生,您知不知道这样的行为很像一个变态。”
时庚也没有反驳,他只是一直在注意着季知书的情绪,反而问道,“你不生气?”
季知书笑嘻嘻地回答,“当然会生气,不过时先生更让我生气的是另外一件事。”
时庚诧然:“什么事?”
季知书捧着他的脸,眉眼弯弯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永远想不起来,你来迟了,时先生。”
“你就藏着捏着,怕我找你讨债是么?”
时庚怔怔地和他对视着,“你想起来了?”
“是,最近情绪有点波动,所以想起来了很久以前的事情。”季知书说,“时先生是想一直打算瞒着我,然后让我误会是么?”
他的眼睛仿佛在说:你在害怕什么?
时庚被盯着有些畏缩,眼神躲闪地说,“你不喜欢,我会改。”
但他并不为自己的所作而道歉。
这是他寻求慰藉的唯一的方式,似乎只有站在暗处他才敢肆意地欣赏季知书,可以直白地观摩他的每一个动作。
他早就病了,叫他一直客客气气和季知书保持着礼貌距离是不可能的。
不过基于此的前提是季知书地疏离。
“时先生答应了可要做到。”季知书说,“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不然我会生气。”
“好。”时庚点头答应。
没过多久,时庚就当着季知书的面叫人拆掉了大部分的监控,除了一些必要保障外,时庚还保证没有特殊情况不会打开。
但是事实上,在某一些方面,时庚有他的执着。
车库里的车都被清空,季知书若是想要出门只能联系私用的专人司机。
时庚仍然可以掌握季知书的行程位置。
但是季知书并不在意,他知道这是时庚所能做到的最大的让步,甚至是一退再退的底线。
季知书觉得时庚对于他似乎有一种特别地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