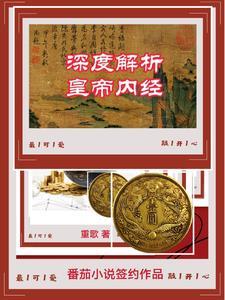极品中文>花月结局 > 第86章(第1页)
第86章(第1页)
“好,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沈夜雪攥上其衣袂袖摆便快步顺着窄道行出,跟步身后之人却很是谦顺,任她扯着衣袖默声向前。
走出幽暗府牢时,庭院朦胧,月冷森森,院中亭台处现出桃花面,她定睛一瞧,黛眉不觉拢紧。
四周艳丽多姿之影,是花月坊的人。
傅昀远闲然坐于亭中,似瞧好戏般正望向她,见着这女子带着府内昔时的门客落荒而逃。
一旁伫立的是那韵瑶与落香,亦兴致使然,观其无路可走。
沈夜雪悠然停步,瞧玉锋门之人已退至边角,公子沈钦被侍从推着轮椅于暗中行来。
阿雪先走,听话。
花月坊行事向来诡谲,论身手自比不上玉锋门,可论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却占得几许上风。
眼下已无法思索花月坊是怎般救下的傅昀远,她心感好奇的是,当初说要攀附玉锋门的公子,竟又回头去倚靠了这位宰相大人。
“你们一个个的,都心怀鬼胎,对本相不臣不忠……”傅昀远笑意盎然地一指沈钦,再指了指她身旁男子,犹如笑里藏刀般微凝眉眼。
“老夫还真是养了一堆的白眼狼……”
“你们莫非以为,今晚入了相府,还能安然而退?”言此微顿,傅昀远倏然大笑,“陛下早已派遣皇城司步下天罗地网,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明争暗斗了数些年,为擒一个叶清殊,那小皇帝竟能与这佞臣和解……
这些人是有多怕叶氏……沈夜雪轻然一松手,随之上前一步,仪态闲适地回望着众人,丹唇徐缓上勾。
罕见昔日的花魁娘子穷途末路成这模样,韵瑶讽笑了几声,末了不忘再向大人恭维上一言:“傅大人高明,这叶氏余孽定要诛尽杀绝了才好,以免再生谋乱,闹得人心惶惶。”
“若我记得无差,公子可是投靠了玉锋门,”淡然回以嗤笑,沈夜雪转眸看向面无神色的沈钦,盈盈柔笑了起,“这靠山还未靠热乎,怎又回首去为傅大人当牛做马了?”
许久未道这冷嘲热讽的应对之言,她都快忘却了,忘了旧时在花月坊中是如何忍受着不得安生之日。
与一群姑娘争着宠,还要谨言慎行,日日临危履冰,如临深渊……她再不愿忆起不堪回首之往。
沈钦闻言微凛着深眸,一身肃冷,对她的挑衅欲语还休,眸色逐渐黯淡:“叛臣叶确麟之子必除之。当年叶确麟作乱天下,为傅大人与陛下的心腹大患。”
“如此凶叛贼子,花月坊代为诛灭,义不容辞。”
“花月坊若能将功补过,本相便不追究以往。”见势冷哼,幽暗目光落至轮椅上,傅昀远肃声提点,又像是在向走投无路的二人仁慈作解。
原是老奸巨猾之臣给花月坊抛下了一条救命绳索,顺着绳索上爬,便能攀回原先的高枝。
如今随着离声的身世被揭,玉锋门成为众矢之的。
公子已然放弃这处高台,顺着风向保命去了。
沈夜雪眉眼一弯,眸光媚然流转,掩唇哑然失笑。
公子这株墙头草是越发推诚不饰了,罔顾傅昀远所言真假,也要听其一命,为于乱世寻得可安处。
她眯了眯双眸,极不客气地再度开口:“公子还真是善于见风使舵,两面三刀。”
“这话我便不爱听了。”
公子能忍,立于一侧的落香可是忍不了,就算面前是公子难以释怀之影,其也要为公子道上几言:“公子曾让你作为京城花魁数些年,受尽恩宠拥戴。而今你竟这般反咬公子,当真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落香,你和她费什么口舌,直接杀了不就好了……”另一旁飘来娇媚笑声,笑语还未飘远,一瞬寒光便直直袭向清艳皎姿,韵瑶长剑脱鞘,发了狠一般朝其直逼而去。
未想一日竟会与花月坊为敌。
沈夜雪倒也无惧,剑光相抵,霎时接下频频袭来的攻势。
此剑招来势极其猛烈,不愧是公子培养的娇花刺客。
她暗暗作想,一人尚可应付,若再加上个落香,她怕是支撑不下。
韵瑶媚眼如丝,妩媚将她观望,剑影不止,唇角透出微许猖狂:“几日不见,想不到你竟能这般为护新主出生入死,之前也未见你为花月坊赴汤蹈火啊。”
话语轻落,又听此媚影讪笑了几瞬,沈夜雪忽感一阵冷风刮过,顷刻之间,眼前已无人影。
韵瑶陡然瞪大了双眼,颤抖着瞥向心口,一把利剑已直扎在心,身子被硬生生地钉上了院墙。
一念惊慌而过,这道风韵美色已殒命于森冷夜色下,徒留令人发颤的死寂。
“你们是何等鼠雀之辈,也敢动她。”
院落一角飘荡出冷冽之音,字字寒凉入骨,引得亭内几人不由胆寒。
言语之人,是在旁静听许久的离声。
“韵瑶!”
下意识喊出口时,落香猛然捂唇,睁着一双撩人心怀的眼眸,瞧着那妩媚身姿已成了一具尸首,汩汩血流仍在滴落而下,恐惧顿时弥漫了开。
趁当下之势撤逃再适不过,沈夜雪断然再扯男子云袖,欲让玉锋门断后,岂料相府已被包围。
府外皇城司护卫若黑云压城般提剑而立,令府邸上下任何一人都逃离不得。
领卫皇城使抬手一挥,高喝一嗓,不计其数的宫城影卫便持剑攻来。
“皇城司奉陛下之命捉拿叶氏残渣余孽,给我拿下!”
现下局势太过不利,纵使身手剑术再高,也不敌如此之多的皇城守卫。
她蓦地回眸,见离声已从地面拾起一把长剑,将她往身侧一带,忽而低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