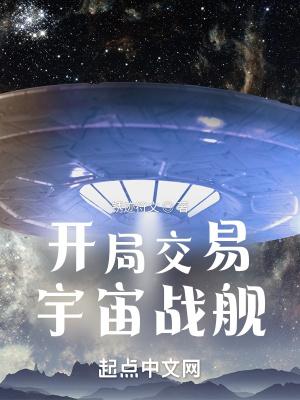极品中文>被迫嫁给丑夫后免费阅读全文笔趣阁 > 第 67 章 调查旧事(第2页)
第 67 章 调查旧事(第2页)
晚上回家吃过饭收拾好后,邱鹤年烧了水,说要洗澡。
炉灶里放了精煤,火烧得很旺,把屋子里烧得热烘烘的。
浴桶里,清言懒洋洋用双臂交叉,垫着下巴趴在桶边,眯着眼睛。
邱鹤年披着衣衫站在浴桶外,正细致地帮他搓洗那头乌黑顺滑的长发。
清言昏昏欲睡,呼吸间都是淡淡的水汽和皂角的味道。
直到身后的男人轻声道:“好了。”
他才睁开眼睛,从浴桶里站起身,邱鹤年扶着他一只手,看着他垂着头从桶里迈出来,腿的线条修长,肌肤莹润,动作间有种小动物似的轻盈和优美。
清言在地上站稳了,屋里虽然足够热,但刚从热水里出来,总还会觉得有些凉意,胸口不由得微微紧绷起来,邱鹤年往那里扫了一眼,之后就拿了布巾给他擦身。
擦得差不多了,邱鹤年就把
()布巾交给清言,要他去床上盖上被子擦头发。
清言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也帮你洗。”
邱鹤年冲他笑了笑,“去吧,等我一下,很快。”
清言眼睛眨了眨,脸蛋渐渐红了,听话地去床上了。
邱鹤年看着他上了床,目光在他背影上细细扫过,在那对儿随着他的走动而被牵动的凹进去的腰窝上,停留得尤其久。
清言弯下腰去够叠在床里侧的被子,油灯放在了浴桶附近,那边的光线太暗了,□□留下的是一片暧昧的二角形阴影。
床边的人终于收拾好了,掀开被子上了床。
邱鹤年适时收回目光,脱去披着的衣衫,迈进浴桶。
热水里浸过身体,有淡淡的熟悉的香味笼在周身,邱鹤年仰头闭眼,深呼吸了一口,身体放松下来。
都洗完以后,油灯挪到床边的桌上,两人一起靠在床头看书。
最近他们看的是本讲各地志怪传说的书,诸如哪个地方在一个下雨天,天上掉下来一条的大黑鱼,下来便屠杀生灵,这时另一条从天而降的大红鱼,为了制止它,在空中与之大战八百回合,把黑鱼杀死以后,自己却也流干了血而死在一个山头上,所以那里的山,土都是红色的。
清言以前觉得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尤其是每次看完一篇,邱鹤年还会给他讲讲故事里提到的地方真实的情况,结合着看就更有趣味。
但他这会儿情绪又渐渐低落下去,怎么都看不进去了。
邱鹤年发现了,于是放下书,问道:“今天看的黄龙戏有意思吗?”
清言点了点头,“好听,也好看。”
邱鹤年又问:“你最喜欢哪段?”
清言回想了一下,说:“那女子和夫君在堤上喝酒唱祝词那段。”
邱鹤年沉吟了一阵,清了清嗓子,竟开口唱道:“一愿郎君千岁,二愿妾身常健,二愿如同梁上燕,岁岁长相见。”[注]
这段戏词台上那女角唱来,是细腻婉转的,邱鹤年的嗓音偏冷冽,此时唱来微微沙哑,竟有种反差极大的清冷、粗犷而缠绵的感觉。
清言看着他,睁大了眼。
邱鹤年笑着抬手在他脸颊上捏了捏,道:“别这样看着我,我该后悔唱这个了。”
清言终于捂着嘴笑了,笑了一阵,又忍不住趴在邱鹤年身上笑出声来,感叹道:“你竟然会唱戏!”
说完,又接着哈哈笑。
邱鹤年无奈地看着他,说:“再笑就对你不客气了。”
清言笑着说:“来啊,我不怕!”
邱鹤年于是就真的不客气了,清言被按倒在床上,发出轻轻的哼哼声。
亵衣松垮垮地被撩开,露出晕黄光线里的莹润肌肤。
脚踝被大手抓住,膝盖碰到了自己下巴颏。
清言笑不出来了,红着脸扭过头去。
邱鹤年垂着眸子细细打量着这具漂亮的身体,明明长着清丽纯真的容貌,那两处颜色也浅淡,但却……。
邱鹤年的眸色越来越暗,他弯下腰侧过脸,离得很近地与清言面对面,清言眨了眨眼,睫毛好像刮到了他的。
男人就这么近地看着他,轻声问道:“现在怕不怕?”
清言咬了咬唇,说:“不怕。”
男人更贴近他,吻轻轻落下,又由轻到重,唇舌纠缠,然后湿润炙热的吻向清言的下巴和脖颈。
过了一会,清言惊地想坐起身,却被男人有力地手重重压着,他用手去推男人的头,却也推不动,只含含糊糊地道:“别……脏……。”
又过了一小会,清言哭唧唧地求饶,“我怕,我怕还不行嘛!”
可说什么也不管用了。
屋外又下起雪来,也许是春天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场雪,寒风呼啸,撞在窗棂上哗啦哗啦地响。
屋里热得像夏天,清言的两条腿好酸,可是他已经顾不上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