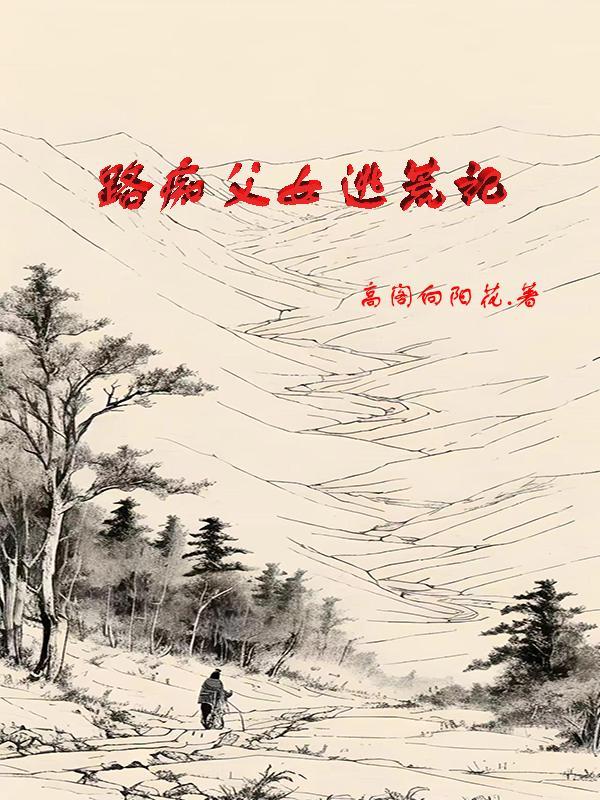极品中文>女配是个万人迷正版阅读 > 第42章 独一无二(第1页)
第42章 独一无二(第1页)
丁舒漫听着他的话,抿了抿唇,那双生动灵气的眼眸暗淡了几分,她语气莫名地说了一句,“陈许凛,你真的很不公平。”
陈许凛低头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语气理智到近乎冷漠,他以为她说的是这次的事,“是吗,我不觉得。”
银色闪电在天边乍现,风云变幻莫测,压抑到极致的墨色,似乎在准备造就一轮新的日月。
温尔没有留手,左渊眼角和嘴角都在不停地流血,甚至开始肿胀起来,空气中弥漫着血腥气,并不好闻,他那张脸在此刻生出几分破损的美感。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她能感觉到自己手指骨节传来的疼痛。
温尔拽着他的领子,从左渊的角度,她那纤细白皙的颈项看起来脆弱易折,不堪一击,但实际上却是她居高临下地望着他,“左渊,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左渊肩膀略微颤抖着,陡然笑了起来,满面血污,神情莫名。
温尔皱了皱眉,只觉得他又在疯,但是电光火石间,她忽然想起一件事,左渊这么清楚当年孤儿院的事,极有可能他也是来自于此。
并且他憎恨的人里面还有一个她,温尔直觉自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她视线落在自己攥着的领子上,因为用力过度,上面满是褶皱,扣子也掉了一颗。
如果想要知道问题的答案,只需要很简单的一步:拉开他胸前的衣襟。
她那双顾盼生辉的眼睛,此刻正专注地盯着一个位置,她指尖微动……
就在这关键之际,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清朗嗓音,“尔尔。”
是温期言出现了,他脸色苍白至极,清瘦的身影在这冷风中,有种凄清的破碎感,单薄得仿佛风一吹就会消失。
视线交织,温尔从他眼里看到了祈求和惶恐,她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像是一个拼命想要握住手中流沙的人,自欺欺人又惊惧不安。
温尔原本要继续下去的手停住了,她不想让温期言难过。
身下的左渊注意到她的视线,笑得颤抖,鲜血顺着他的嘴角流下,他猛地拍开了温尔的手,“啪!”
他手劲很大,温尔白嫩的手几乎是瞬间就红成一片,她沉默着,只是缓缓松开了手,“两清了。”
那个欠着的过肩摔,温期言的病,都止于这一步。
她那张清丽脱俗的脸自始至终都很平静,只除了那双眼睛偶尔会泄露几分情绪。
然而就在她准备抽身离开时,透过左渊那略微散开的衣襟,温尔看到了他锁骨下方的胎记,颜色偏粉,形似花瓣,独一无二的标志。
温尔怔了一瞬,她只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这样的胎记,那个当年在孤儿院没有被她选择的小男孩。
原本正朝着温尔走来的温期言,脚步霎时停住,他并不知道胎记的事,但是他了解温尔,也熟悉她的每一个表情,温期言心头忽然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慌。
其余几人不知道到底生了什么事,但这股奇怪又诡异的气氛感染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丁舒漫不解地挠着头,陈许凛依旧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表情,谢子都若有所思,周故澈则是眉间略有担忧。
“咳咳咳……”
左渊笑得颤抖起来,像是有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他眼里都是嘲弄和讥讽,配着那张满是血污的脸,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
温尔看着那道胎记,终于回神,把人松开了。
“咳咳……温尔,你从来令人恶心。”他一只手撑着地面,另一只手,抹掉了嘴边的血,狠厉地说道,“你和他都是。”
温期言鸦羽般的睫毛颤了颤,手心凉。
温尔盯着左渊那张脸,试图找出一点记忆中的轮廓,然而只是徒劳,当年瘦小的男孩已经长为身姿挺拔、不羁张扬的少年,判若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