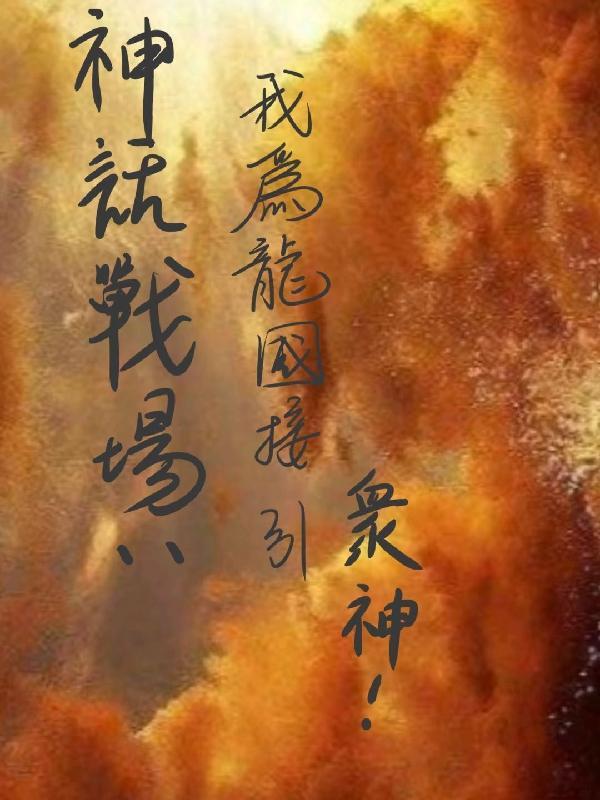极品中文>送情郎原唱 > 第89章(第1页)
第89章(第1页)
直到宋清升上初中,宋欣梅才渐渐恢复过来。她不仅恢复了原先的生气,更是在绝望中生出一股傲气,拿出所有积蓄在镇上开了家面粿铺,此后一心都扑在生意上。
她对宋清不再百般照顾,不再嘘寒问暖,不再哀声抱怨,两人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见不上一面。
但对她却多了一个要求:“一定要考去北京,给妈妈争口气。”
后来宋清每每失眠躺在床上,都会思考造成这一连串悲剧的原因。
当把自己从故事中摘除掉,看问题反倒能更加客观些。
所以她翻来覆去地想,觉得每个人都有错。
譬如本不重男轻女的外公和外婆却迫于外界压力,在宋欣梅16岁那年给她生下了一个弟弟。
生下宋辛明后,外公宋则柏为了多挣些钱,便跟着邻村一个包工头在外四处奔波,却因为盲信熟人,被拖欠了近半年的工资。
宋欣梅看着自己年幼的弟弟每天只能就着罐底的一点奶粉喝米汤,实在过意不去,擅自退了学,跟同桌一起去镇上的纺织厂打工。
日子刚刚好起来,宋则柏却因为工厂事故断了一只手,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他连休息都不曾,一砖一瓦盖起了小卖部,却还是害得宋欣梅被人嫌弃。
因为急于将已经“高龄”的宋欣梅嫁人,外公和外婆并未仔细调查刘汉国的为人,只听中间人的三言两语,就匆匆定下婚约。
在宋欣梅生宋清的时候,因为本地有习俗说,生孩子的时候如果娘家人在场,就会导致孩子难产。所以哪怕心里再着急担心,宋则柏和刘惠兰还是连一步都未曾踏进医院,把第一次面对生育的女儿独自一人留在了空荡的产房内,叫她独自去面对。
而刘汉国那不把媳妇当人看的亲妈,明明自己也是辛辛苦苦由媳妇熬成婆,却学不会以己度人。
但宋清自己也知道,即使人人都有错,但他们每个人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常常也是无可奈何。
他们也不是非要把自己的人生过成这副模样的。
除了她那无德无能的亲爹。
宋清将共享停在路边,甚至连车都忘了锁,拨开面粿铺外围观的人群,长腿一迈就往宋欣梅面前走。
你算个什么东西?
如果说宋清和18岁那会相比,成长了什么的话。
那大概是懂得了,不抱怨过去,不寄托希望,不祈求怜爱。
所以,她既不会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有义务去为谁争一口气,抑或是完成谁的任务,也不会置身事外地冷眼旁观怀胎十月生下自己的人被欺负。
和宋欣梅的所谓母女关系或许在她下跪求自己改志愿的时候就已经荡然无存,但除开母女关系,她们还是家人。
平日里各自安好,互不干涉,但遇事必然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家人。
宋欣梅像是很惊讶宋清会出现在店里,手扶上她胳膊将人推开:“你来这里干嘛?给我回家去。”
她小声说着,就好像小时候每回她和刘汉国吵架,都会先把她赶回房间那样。
宋清挡在她身前,被推了两下没动,而是掏出手机打开录像:“我听说店里有人闹事,过来凑个热闹,顺便取证,省得到时候砸坏了店里什么东西,有人还要耍无赖不肯赔钱。”
刘汉国不傻,自然听得出她是在点自己:“你怎么说话的?”
宋清摄像头直怼他脸:“用嘴巴说的,怎么?你不是吗?”
刘汉国:“有你这么跟自己亲爸说话的吗?”
宋清无视了他的质问,扭头问宋欣梅:“他刚刚在这里吵什么?”
没进店之前,隔着条街宋清都能听见刘汉国歇斯底里的质问声,还是跟20多年前那般暴躁易怒。
宋欣梅却不想她插手这种事:“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回家去。”
“没事,我就听听,你们聊你们的,不用管我。”宋清嘴上这么说,手却依旧举着手机,摄像头明目张胆地对着冷脸对峙的两人,像个没有分寸感的战地记者。
她不是来劝架的,也没有帮腔吵架的能力,她只是来确保自家财产免受损害。
宋辛明刚疏散完一众看热闹的无关人员,又给了几百块钱让店员先去找家店喝杯奶茶,才把卷闸门拉上。
店里陷入昏暗的同时,房顶的日光管也被按亮,宋辛明走近朝刘汉国冷声喝道:“你来干嘛?”
原先的嘈杂人声被隔绝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几台还在卖力工作的冰凉机器,以及三个眼神语气比机器还要冰凉的人。
刘汉国环顾四周一圈,颇有些羊入虎口的后背发凉感。
十八年前宋辛明拎着把斧头跑去他家喊着杀人偿命的情景此刻仍然历历在目。
“我来干嘛干你屁事。”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却还是嘴硬。
宋辛明摆手让他滚:“不是来买东西的就赶紧给我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
刘汉国却不理他,目光径直转向宋清,问:“你弟呢?叫他出来。”
宋清除了一直拿手机拍刘汉国外,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没听见,甚至连正眼都不愿意给他。
“不是——”宋辛明朝他肩膀使劲一推,往前一步挡在宋欣梅和宋清面前,“你到底是来干嘛的?”
“来干嘛?我带我儿子认祖归宗我来干嘛。”
刘汉国这一趟回棉阳,原本只是想给那位棺材泡了水的远房亲戚迁坟,可实际到那一看,才发现自家也有几个关系亲近的长辈的坟墓建在附近,若是不趁此机会一块儿迁走,怕夏天雨水多,过阵子又要无端遭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