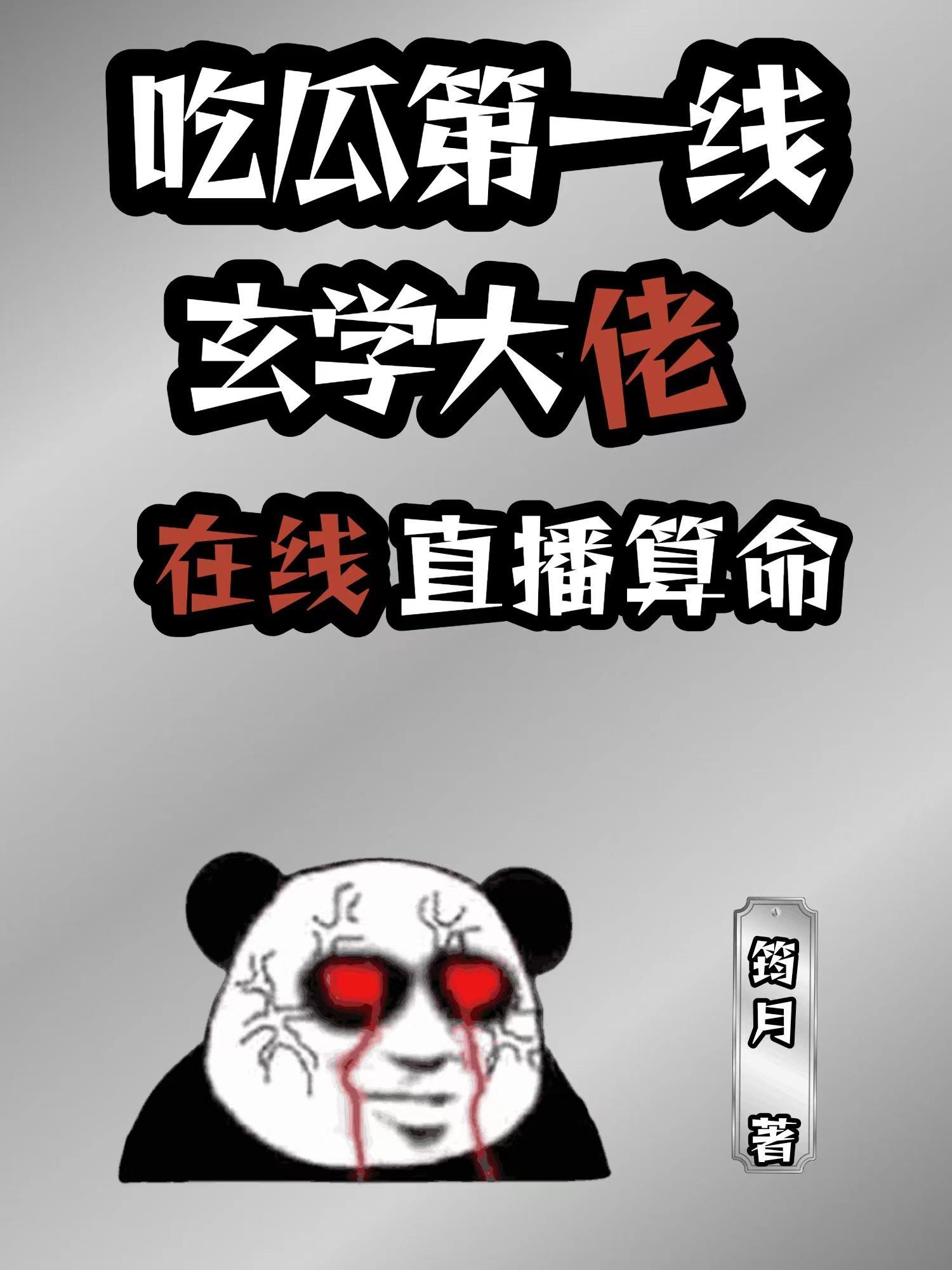极品中文>青乌子真的存在吗 > 第51章(第1页)
第51章(第1页)
他的唱腔与表演都极为精致,扮相令人惊艳。既有出色的天赋,又有坚持与努力。在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之后不得已进入尚云社,靠登台亮相唱戏谋生。没了后台之后,很快遭到了师兄弟的嫉恨,处处受到排挤,后因尚云社老板不敢得罪权贵竟将他推出去陪酒。
他不甘忍受军阀头子、富商大贾的污言秽语毛手毛脚,卖了祖宅后远走他乡,最终停留在了水城苏州城,被云游子收留。从那之后他一心只攻医术歧黄之术,不再接触戏曲。
直到秦俊儒二十三岁那年,在小师弟洛九衣十六岁的生辰。为了哄病榻上的小师弟开心,他翻出了压箱底的淡粉色绣花帔帛,绾插簪,戴上水钻头面,扮成未出阁的娴静少女杜丽娘,唱了一段《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唱功虽不及年少时,也是华丽婉转,再加上婀娜多姿的身段舞步,看得小师弟拍手叫好,脸色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洛九衣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师兄曾经厌恶重拾戏子的身份,连最喜欢的戏曲都不愿去听了。不过是为了博自己病榻上一笑,放弃了心中的厌恶,扮起了青衣,在他面前咿咿呀呀地吊嗓子,学女子向他抛媚眼,让他在那刻忘记了病痛笑出了眼泪。
“师兄……”洛九衣喃喃地喊道,两眼半睁却没见到秦俊儒,入眼竟是莫名有点熟悉的朦胧的潇湘馆景象,有门有窗,回廊下挂着鹦鹉,纱窗外竹影吐翠,摇曳婆娑,偶一开窗,竹叶伸进屋里,清雅凄清。
“消磨却三生绮陌天,领受了半晌阳和境,一霎风光,做一霎凄凉景,可怜他谪下蓬山,移来绣岭,本来是孤苗悴叶恹恹损,禁他雨雨风风,酿就了红颜薄命,空留这护花幡拂护花铃,尚兀是送丁丁隔远声……”
听秦师兄说过,“黛玉葬花”唱得好的人会采用这样的低弦低唱,韵味醇厚,低回婉转,稍稍一用劲,就挑了上去,这样高低之间,增强了戏曲声腔的情感色彩。
图门玉卿本就是美人胚子,身材高挑,面貌清秀,扮出戏来妩媚艳丽,大眼睛双眼皮,脉脉含情,一个转身一个抬眼,就惹得观众拍手叫好。
洛九衣透过纱幔看过去,图门玉卿扮演的林黛玉,面前搁置着一张太师椅,太师椅上大马金刀坐着一个赭红色军装的男人。显然这屋子里除了纱幔后软榻上一动不动的自己,就只有那军官是唯一的观众了。图门玉卿单独为那人唱了一出戏。
洛九衣眨了眨眼,能看到那军官眉毛拂天仓,印堂接中正,双颧并起于峰峦。陈书贤告诉过他,若眉如新月,而拂天仓者,则其主聪明贤能,近贵也,若印堂宽隆,上接中正,而光润平泽者,利于官禄,若二颧高,其人有呼聚喝散之威也。
他声音洪亮,元气充足,鼓掌赞道:“好!玉蝶姑娘果然是个妙人儿!赏!大大的赏!”
图门玉卿曲膝谢恩,细碎步伐走上前,嫣然一笑:“荆将军,玉蝶这就告退了,还请将军务必好好享用屋里的另一个妙人儿,别辜负了玉蝶的良苦用心。”
赭红色军装的荆将军哈哈大笑,大手拍上图门玉卿的肩膀:“玉蝶姑娘有心了!很好!下去领赏吧!本将军不会亏待你的。”
“是!谢荆将军。”说罢又伏了伏身,一边轻笑着一边走了出去,还特地关紧了大门。
大门砰的一下被锁上,洛九衣心尖一颤,想要挣扎却浑身都动不了。那荆将军从太师椅上站起身来,甚是威武雄壮,像一座大山似的,大踏步迎着软榻走上来,洛九衣心跳如擂鼓,与那荆将军双目俩俩对上的一霎那他的心脏几乎跳出了胸腔。
荆将军走到软榻跟前,居高临下打量了他几眼,忽然猛地抬手掀开了薄被,洛九衣一下子闭上了双眼,下嘴唇咬得紫。
等了好一会儿没再有任何动静,洛九衣颤颤巍巍地掀开了眼皮子,现那荆将军退后几步,双手交叉在胸前,见他睁眼后才道:“原来是个带把的,还当是个女人咧。看你这样子,不是戏子伶人也不是劳什子小倌啥的吧?不过这幅绝色,老子一个不喜欢男人的看了也心跳得厉害。”
洛九衣努力了半天才从喉咙深处挤出零丁点声音:“这里……是哪里……”
荆将军皱了皱眉头,转身走到圆桌前倒了一杯热茶,拿到软榻前的案子上放下:“来,喝一口润润嗓子,估计你也是吸了那小娘们儿的寐烟了,现在身上没啥子力气吧,再等会儿就好了。玉蝶那女人年纪轻轻可不简单,头上的空心簪子珠钗里时常装着寐烟的烟尘,一触到活人就会随着活人的呼吸飘进口鼻,大概有七八个时辰的药效吧。”
洛九衣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瞧着这位长得像只猛虎似的荆将军:“你……果然不是坏人?”
“噗……哈哈哈哈!”荆将军听了他的话捧腹大笑,像是在嘲笑他的天真烂漫,“这位小公子,恐怕是供养在深宫里的小贝勒吧?难不成姓爱新觉罗?啊哈哈哈!”
洛九衣被他笑得有些尴尬,耳根子微微红,干咳了一声道:“玄门中人不打诳语,在下的的确确是八旗旗人后代,出自上三旗正白旗,旗主乃是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
荆将军笑声嘎然而止,像是嗓子口被堵住了似的,一下子蒙住了:“皇?皇太极!”
洛九衣手指小幅度地抽动,指尖的力度仿佛又回了过来,他开口道:“可惜眼下被称作八旗子弟的,自清末开始名声就不佳,只贪图享乐,男的打茶围,蓄画眉,玩戏曲表演,赌博,斗蟋蟀,坐茶馆,一天到晚尽是忙着吃喝玩乐。就连女子也各有各的闲混过日子的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