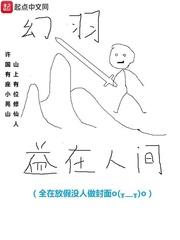极品中文>被迫成为魔君的白月光免费 > 第75章 在其板屋七(第2页)
第75章 在其板屋七(第2页)
顾景尧淡淡道,“你且绣着便是了,无论你绣的多不堪入目,多不是个东西,都自然有用处。”
裴娇似乎有些悟了“你是要拿去辟邪”
“”
一直于偏殿外等候的卓念慈没忍住逸出一声笑。
他瞬时觉得不妙,果然,一抬眸便对上珠帘后青年冷若冰霜的目光。
要死要死要死
而裴娇恰巧也注意到了偏殿等候的二人,知道他们或有要事禀报。
恰好她不愿与顾景尧同处一室,便刚好寻了个借口开溜“魔君有客,我便不宜于此了,先行告退。”
随后逃似的远离了那可怕的针线,像是一阵风般消失了。
卓念慈觉那位年轻魔君的面色又阴沉几分,顿感不妙,恨不得抽自己一耳光。
而乌若则是悄然望向殿内还未烧完的一柱香,心中叹息
每每裴姑娘午膳后再魔君寝宫内绣花样的这一柱香时刻,便是魔君一日内心情最为愉悦的时刻,这栖云涧合欢宗宗主可真是没有眼色。
卓念慈这厢还在担惊受怕,他最引以为傲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奉承功夫却不敢在身前这人面前卖弄。
心里又因先前裴宁的一番话心虚得很,只得磕磕绊绊地不知所云。
“合欢宗自始至终都效忠于魔君,赤胆忠心苍天可鉴”
言罢,他的一腔豪言壮语被里头自顾自饮茶的人冷不丁打断,顾景尧眼神透着凉薄与不耐,言简意赅道“我不需无用之人。”
“鬿雀。”
他唤出一声,暗处的映出一抹飞鸟的影子,随后那抹影子便如潮水般化作人形。
鬿雀跪于地,“魔君大人,有何吩咐”
卓念慈见了鬿雀,吓得更是大惊失色。
他先前打听过,这鬿雀,就是专门负责处理宫内叛徒的。
这女人本就是凶兽所化,手段也格外狠辣,自己要是落在她手里
卓念慈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就在此时,身侧一直静默不语的纸鸢突然柔声开口,“魔君大人,宗主所言皆是肺腑之言,妾身与宗主此番前来,实则是为魔君大人尽忠的。”
卓念慈微微一怔,就听纸鸢妙语连珠道,“魔君大人英明神武,统领魔域只是时间问题,合欢宗在此方面只得尽微薄之力。”
“纸鸢修为不高、学艺不精,但身为女子,却颇懂女子心事。”
“若是魔君大人为方才那位姑娘而烦恼,纸鸢愿为魔君大人排忧解难。”
她语调轻柔,恍若吴侬软语。
在觉那居高临下的魔君大人终于注意到她,沉沉的目光终于落在她身上时,她的心跳猛地加快。
半晌,只闻一声嘲弄冷笑,顾景尧阖着眼皮似笑非笑道,“你算是什么东西,也配和她相提并论”
纸鸢捏紧手心,垂下头飞道,“奴身份低微卑贱,自然不算什么东西,但若能为魔君所用,哪怕创造一点点价值,也是奴的荣幸”
说至此,她已是冷汗涔涔,只能凭借着自身多年来对人情世故的通透抱着豪赌的心态道,“魔君,一个心思并未在您身上的人,哪怕用多名贵的外物也是留不住的。”
“喀啦”一声,檀木桌上的茶具瞬时化为齑粉。
顾景尧昳丽的面庞瞬时阴云密布,令人喘不过气的威压瞬时席卷整座寝宫。
正当卓念慈心中大喊吾命休矣之时,又听那人出一声短促的笑。
他缓缓站起身,高挺的眉骨于面中落下一片阴影,沉声道,“继续说。”
纸鸢早已被强大的魔息吓得不敢动弹,以额头紧贴地壁,声若蚊蝇:“奴、奴虽不懂其他,但是对于姑娘家的心思还是十分透彻。”
“或、或许能使一些小手段,让那位姑自此以后对魔君您死心塌地”
最终,卓念慈显然没想到自己能够活着走出。
他摸着自己尚存的脑袋,忍不住感慨道,“我的心肝纸鸢,不愧没看错你此番脱险皆是你的功劳,回去本宗主定要好好赏赐你。”
“不过这位魔君如此难对付,你都和他说了些什么”
纸鸢亦有种豪赌获胜劫后余生的解脱感,不由得莞尔一笑“宗主谬赞了,纸鸢不过是对儿女情长这些了得的多,无非就是懂得姑娘家的心思,知晓如何追姑娘罢了。”
“弟子只是实话告诉那位魔君,追求姑娘的方法不简单,若是想要那位姑娘动心,可不能光是给予馈赠,更要令她有危机感。”
“若是能有另外一个女子出现在魔君身旁,便是这样演一场戏,这位姑娘说不定就会吃醋”
言至此,她微微伏身一拜,“故而弟子为了合欢宗,便主动请缨去做这样一个导火索,借此接近魔君讨魔君欢心,也自然能对南镜这边的情况了解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