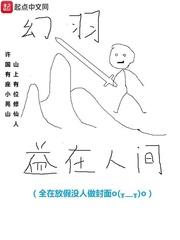极品中文>公主病拆小马宝莉卡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
他又转头问倪雪:“你吃什么?”
倪雪环顾店面一圈,欲言又止。
一见这人露出这种表情,蒋冬河便顿时心下了然,这是又犯病了。等这人挑三拣四完毕,估计可以直接吃晚餐。于是他不再过问倪雪的意见,对老板说:“再来份一样的。”
他们来到外边的空桌前,蒋冬河没那么多讲究,抽出塑料凳子坐下。
对面倪雪不如他这般干脆,看着眼前油腻腻的桌椅,纠结再三,还是没能狠下心。
蒋冬河不管他,也不说话。
最终,倪雪还是敌不过脚踝处传来的疼痛,拿起纸巾擦了擦凳子,勉为其难地坐下,就是看起来有点如坐针毡。
两人面对面坐着,气氛一时间又变得沉闷。不同于以前总是倪雪找话题,蒋冬河一反常态地先开口:“倪雪,我知道你这人臭毛病多,不过你提前想好,住我这儿可以,但老子不惯你那些毛病,待不了就滚。”
挺严重一句话,被蒋冬河故意讲得很直白。之前做班委的时候他必须耐心服务同学,以至于大家都以为他和善又热心,事实上,只有蒋冬河自己清楚他到底是什么脾气,现在他没必要迁就谁,自然不会跟倪雪太客气。
倪雪撇撇嘴:“你又这么凶……”
蒋冬河直言:“我本来就这样。”
果不其然。这人在外人面前都是装的,只有他识破了蒋冬河的真面目!
倪雪干巴巴地“哦”了一声。
蒋冬河:“我还要约法三章。”
炒饭还没端上来,蒋冬河掏出手机,用备忘录起草。
一,倪雪居住期间,需与蒋冬河共同承担租金及水电费等各项费用。
二,倪雪居住期间,需与蒋冬河共同承担各项家务,如洗碗,扫地,倒垃圾等。
第三项还没立刻想出来,蒋冬河琢磨片刻,索性写下:三,一切听从蒋冬河安排。
倪雪对前两条尚且没什么异议,直到看见第三条,险些从椅子上跳起来,“你怎么能这么不讲理?!”
蒋冬河淡淡道:“对,就这么独裁。”
倪雪气得脸颊都鼓了起来,像个包子。蒋冬河心里有点想笑,把手机递给倪雪:“想好了就在上面签字。”
虽然倪雪抗议,但显然抗议无效。在手机屏幕上签下名字的时候,倪雪忽然感觉自己像杨白劳,而蒋冬河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黄世仁。
又等了十分钟,两碗炒饭被服务员端上桌。街边小店的份量很大,直接拿海碗盛,油润的饭粒甚至冒出一个小尖,看起来相当顶饱。
蒋冬河拿起一次性竹筷,拆开包装,将两根筷子相互摩擦几下,去除上面的毛刺。倪雪跟着蒋冬河学,动作略显生疏,做完这些,他试探性地夹起一口米饭。
外边餐馆总是重油重盐,倪雪口味偏清淡,吃了两口便不再碰,“我不想吃了……”
“爱吃不吃,没人管你。”
对面的蒋冬河注意到倪雪早早就放下了筷子,一碗饭几乎没怎么动过,他打定主意要惩治倪雪,自己吃完就起身付了账。
在前十几年的人生里,倪雪极少有这样哑口无言的时刻。即使他是不占理的一方,也忍不住想与对方辩出个高下来。偏偏,在蒋冬河面前,往日的牙尖嘴利全部失效,倪雪憋了一肚子话,竟找不出一句能回应。
他只能拿出手机,恶狠狠地把给蒋冬河的微信备注改成“凶巴巴”。
他们的冷战结在回到单元楼门口时结束。
受伤的那只脚不敢着地受力,倪雪看着眼前的楼梯,迟疑地停下脚步,在心中盘算他能不能单腿蹦上去——蒋冬河家住三楼,应该也还好吧?
结果倪雪到底还是高估了自己,心惊胆战地停在第五层台阶。不行,他就剩一条健全的腿,可不能再轻举妄动。
蒋冬河走在倪雪前面,回头看他一眼,不知道是冷嘲热讽还是幸灾乐祸,咳了一声,问道:“用我背你么?”
开什么玩笑,我倪雪就是累死,死外面,从楼梯上跳下去,也用不着蒋冬河来背!倪雪当即回绝:“……我自己能行。”
“真假啊?不行别硬撑。”蒋冬河直言,“少废话,上来吧。”
“……”倪雪又一次哑口无言,终于小心翼翼地趴在蒋冬河的后背上。
他看起来瘦,但绝不是瘦弱,再怎么说也是个成年男性,身高摆在那里,身上还有锻炼过的痕迹,体重不算很轻。
“重吗?”倪雪问。
“还好,跟想象中不太一样。”蒋冬河语气如常,气息均匀,脚步也很稳,“你平时做什么运动?”
“马术,”倪雪继续介绍,“我自己的马叫Hidalgo,一匹阿拉伯马,通体雪白,特别漂亮。”
“听不懂,说点亲民的。”
“冬天滑雪,夏天游泳。”
蒋冬河笑了笑。游泳他倒是会,村里以前有一条河,男孩子皮实,常常下水玩,在那自学的。
透过薄薄一层T恤,倪雪再次清晰地感知到蒋冬河的体温比他更高,有种蓬勃的生命力。放在以前,倪雪绝对想象不出他与蒋冬河之间会有这么亲密的举动。
他的双臂环住蒋冬河的脖颈,如果他微微侧头,嘴唇就会蹭到那一片的皮肤。
不,不对……倪雪忽然想起来,他和蒋冬河的距离第一次这么近,其实是在高中。
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差,在校园里偶遇都要把对方当空气。
有一次,倪雪听说蒋冬河在校外揍了人,直接把对方揍进医院,却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后来,倪雪还是从狐朋狗友冯博承的口中得知了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