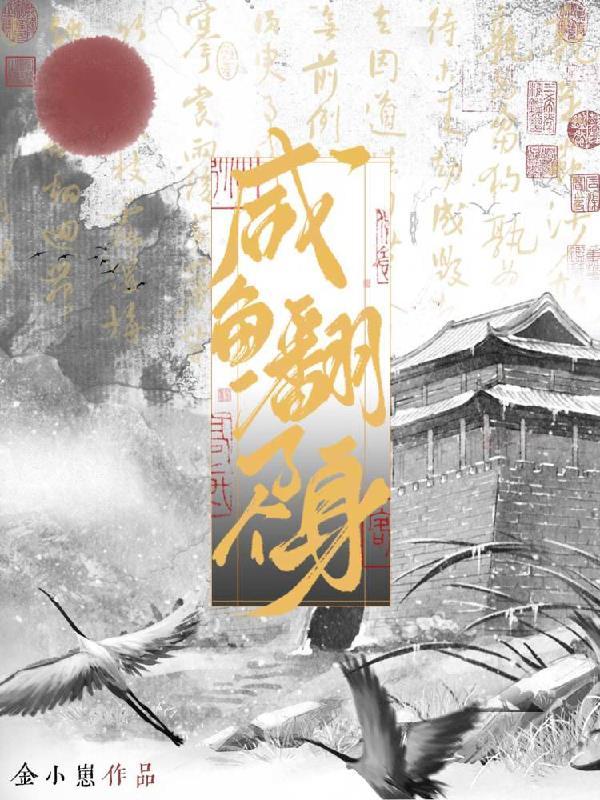极品中文>我不能做小三 > 第3章(第1页)
第3章(第1页)
两人通行只开半扇的门有些拥挤,我站在原地未动,同时陈揽朝察觉到对面来人,停住脚步,后退半步侧一下身子。
他自始至终低着头,礼貌是骨子里的教养,对谁都一样。
我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反应,思来想去没有勇气打招呼问好,更何况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谁又记得谁,他茫然又不解的眼神是对我的凌迟。
于是我浑身僵硬站在原地,放空脑袋在思考先迈那条腿为好,或者干脆两条腿蹦着进去得了。
待他耐心告罄,将要抬起头来时,我猛然回神,装作淡定走进去,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任人操控,控制我的人是个手脚不灵活的大傻子,陈揽朝一定能察觉出不对劲。
我背对他等了一会儿,重新听见动静已是远去的脚步声。
停顿的几秒他有没有回头看过来呢?
我望着他离去的潇洒背影,看他将手搭在于山肩膀,躲开肥头大耳的男人向地下车库走去。
水珠顺着侧脸汇聚在下巴,我撕扯纸巾用力把脸擦得泛红,在一众护手霜中挑挑拣拣,直奔着最后一支茉莉香味去的。
为会馆积极献身,拿个护手霜不过分吧。
大理石板有个亮亮的东西,在头顶璀璨的吊灯映衬下闪着银色光辉,我捏起来看,还带着体温的戒指刚摘下没多久。
联想到陈揽朝有婚约在身,我猜大概率是他洗手时摘掉的戒指。
五月份天气褪去寒冷,傍晚下了一场雨带来几分凉意,长廊通往地下停车场刮着邪风,空旷的地方灯光昏暗,我追上前面两个人的脚步。
“陈先生。”
陈揽朝转头看过来。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近,过快的心跳轰击耳膜,克制自己的语气保持平缓,“陈先生,您的东西掉了。”
摊开的手掌心躺着一枚素戒,平平无奇,没多大花样,我能捕捉到他眼底一闪而过的诧异。
不是他的吗?
还是他不想要的。
陈揽朝双手插兜,往前走了几步。
原本我与他站得位置不过两步的距离,这样一来,他几乎是站在我跟前,指尖擦过掌心捏起戒指。
等客人离开后再退场是必学的规矩,我索性没动弹,他也没动,自然地戴上戒指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做这行的在外在内有两个名字用以区分,知道他并非问的化名,我依然回答他,“柳寒。”
他顿了顿,像是早有预料,“谢谢你,柳寒。”
“外面冷,你回去吧。”
我点头应下,正欲转身,被陈揽朝叫住,随后一片阴影欺压过来,我感受到他的长臂绕过身后,像是隔空的拥抱。
呼吸若有若无地喷洒在我颈项,双肩一沉,他将手臂搭着的风衣披在我身上,细长的手指扣好前两颗纽扣。
陈揽朝弯了弯眼睛,“舞跳得很好看。”
我忘记当时有没有回他一句“谢谢”。
于山光着腿还在那边冻着,他合时宜地打了个喷嚏,看向我的目光挑衅而不友好。
看我有什么用?衣服在我身上,还期望我脱下来给你?
估计是把人晾在一边时间太久不合规矩,陈揽朝和我道别,让我快点回去外面冷,长腿一迈先行上了车,于山紧跟其后绕过车身坐在副驾驶。
我看着黑色奔驰的尾灯渐行渐远,驾驶室的人似乎对我笑了下,也许是我的错觉。
头顶的灯泡接触不良,秋风吹淡了幽香,我捏起领口深嗅他的味道,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他好像没有认出我。
他买我
于山对我怨念颇深,闹来闹去那点破事全给别人看了笑话去,他摆明态度公然与我对峙,也不嫌丢人。
我另外有学业,所以待在会馆的日子短,仅周末两天的下午和晚上有空过来,跟其他人都是仅打个照面的关系,除了杜月见没个交心的朋友。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我没有心思深究于山烦我的原因,因此待我知晓内情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事。
事情源头尚可追溯到刚来报道的那天,荣姐正要给我安排一个空余休息室,不料被几个办事不利索的员工绊住脚,她转头吩咐注意事项去了。
一条长廊数十个休息室,好比高中待的宿舍,没特意标明专属名字,凑巧的是我就那么傻不愣登走进于山的休息室。
当时于山人气高,设施、衣服、搭配是顶级的,我坐在沙发边缘东瞧西看,经理火急火燎推开门,把一个醉酒的男人往房间里搡。
一介土包子哪见过这种架势,经理关门之前提醒把人哄好,我看上去很像会哄人的吗?
脸朝下睡着睡着窒息那可不妙,我挪动男人肥壮的身体,死沉死沉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放平在沙发上。
我对醉酒的概念是从继父那里得来的,他醉不醉一个样,而且躺着的这人穿得正式,一看就是贵客,稍微懂点规矩也知道不能怠慢。
刚撤手准备离开,他哪里还有一副醉酒样,苍蝇搓手似的抓住我的手。
一股恶寒从相触的地方顺着脊柱直升头顶,炸得我满头烟花,顾不得礼仪,直接哭天喊地抱头鼠窜。
要是让我做这种事,那还不如去给人刷盘子洗碗来得实际。荣姐好说歹说,答应我不接客才勉强留下。
后来听说事没办成,搅黄了于山的生意,他原本要拿完钱赎身的。
身上背负的罪孽感太重,我过意不去,偷摸塞给他算作补偿,导致我比于山还熟悉他的门锁密码。
于山硬气得很,强势拒绝我的钱和道歉,当众说我给的钱来路不明,他不稀罕脏钱,也不需要虚伪的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