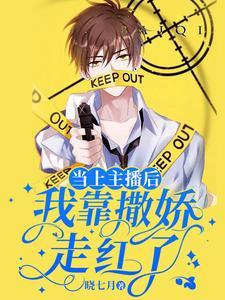极品中文>被动成为第三者怎么办 > 第70章(第1页)
第70章(第1页)
然而今天晏冷淡给人的感觉却似乎不太一样。
忙碌而奇怪,没有低气压,没有冷得掉渣的语气。自他跨进门,至始至终只有一种冷淡而随意的感觉,不锋利,但轻而易举地就能拒人于千里之外。
哪怕韩深与其共事多年,有着直面一线的不凡经验,身处此情此景他也猜不透晏冷淡的心思和意图。
“没有了。”韩深老老实实地说。
确实没有了。他只隐约觉得于玚那天穿的衣服好像在哪里见过,但具体是在哪里,韩深并没有头绪。
这也是他之前未曾言明的主要原因。
既然没有印象,就说明见的不多,亦或是并不重要,是私事。
倘若是私事,这就不是他能插手的范围了。
晏冷淡凝神盯着文件看了半晌,目光尤其落在刚刚钢笔勾划出的字眼间。他漫不经心地转了下笔,动作轻巧、视钢笔的重量于无物,旋即又在空白处留下一行批注。
“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
“给我订一张去京城的机票。”晏冷淡闭着眼,一进车内就下达了指令。
秦明月被他毋庸置疑的语调愣了一下,但还是很快就手脚麻利地打开手机和相关软件,一边查找一边为上司沟通。
“老板,需要为您腾出时间吗?”秦明月下意识问。
但回应他的是短暂的沉默,仿佛空无一人的回答。
坐在驾驶位上的特助迷茫地抬起脸,去看后视镜映出的男人。只见自家说一不二的顶头上司闭着眼,纤细秀美的手指捏着眉心,他以为晏冷淡没听见,便又重复了一遍:“老板,需要为您腾出时间吗?”
“十天。”年轻的执行人说了一个数字,但又很快否定了:“不,尽量都空出来吧。”
“好的老板。”尽管对这样一言不合突然翘班,一翘就是这么久的骚操作满心空白,但已经被下放基层磨练得已有心得的秦明月还是茫然地应了,并将原话传递给相关的秘书和高管。
他满心吐槽和疑惑,自然不知道靠在后排座椅里,闭目养神的男人心底的种种翻涌。
他的脑海里在这时无端地想起一两个月前,那个在高山庄园的雪夜。
晏老爷子的声音发沉发冷,但直到如今晏冷淡才发觉里面可能浸的是彻骨的冷意,势如破竹般划过他的心头,不忌于是否会留下什么伤痕。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你不是这样的人,对吗?”
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一向不管他的老人忽然说出这种话?
只是单纯的路修远被他带走的失踪,是于玚和路修远的关系吗?
——还是其他更多的什么?
在黑暗下行走的过往赋予他的不止是洗不去的血腥痕迹、黑暗底色,还有对于危险的直觉,和敏锐的判断。
在飞机上,晏冷淡低敛着眼眸,薄薄的嘴角忽然挑起一个笑来。
是冰冷的,锋利的,瞬息之间挡不住的森冷阴郁倾泻而出,犹如连环作案的杀人狂魔,气势惊人。
他那时是如何回答?
晏冷淡只身下了飞机,穿的是西服正装,拿的是毒蘑菇电脑包,手腕处若隐若现的是名贵腕表。
他步伐从容,脸色冷淡,仿佛只是参加公司外派的都市精英。不仓促,不忙碌,时间充足。
“对,我不是。”
慷慨的承诺就像一根攥得紧紧的牢绳,坚固到有几分残酷地狠狠拴住了大脑所有的情绪,同时也唤醒了身体里沉睡许久的暴虐因子,随时跃跃欲试着出没。
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发出轻微的响声。
男人站在门边,阴沉沉的眼居高临下地扫过一室漆黑。他知道,路修远不在。
他将钥匙随手扔进口袋,带上门。
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晏冷淡孤身一人静静地立在黑暗中,他那出色的夜视能力令他能够清晰地看见这个房子里的每一处细节:真实,温馨,自然,可靠。
他看见的是白色的、毛绒绒的厚地毯。因为晏冷淡不爱穿鞋,过于热爱光脚踩在地板上,这才让路修远无奈地在家里铺了一层这样的地毯。
于是他拖下鞋,穿着白色袜子的双脚踩在上面,他没去看门边排排坐的毒蘑菇鞋子,或许太锥心。
晏冷淡如同参观浏览一般,悄无声息地在这间屋子里行走,捕捉着每一处曾经熟悉至极的细节,没有先去看自己最在意的东西。
男人走到客厅,看见那个灰色沙发,他记得路修远曾在那里几次躺在他的身下,长腿支在他的腰间,他们在那里做|艾,在那里亲吻。
他还看见沙发旁边大理石桌几,那里的边角都被路修远的温柔包裹,因为晏冷淡的小腿曾几次无意间撞上过,最后被年长的爱人发现。
晏冷淡抬了抬下巴,顺着烂熟于心的方向看见了餐厅。那里是大理石长腿餐桌,同色系吧台,还有半开放式的厨房,隔着厚实而干净的玻璃门就能看见里面收拾干净的厨具。
路修远的身影曾一次次地在这里出现,苦恼地翻阅不同薄厚的菜谱,为上面的步骤和用量在心里思考。有时晏冷淡走过去,从背后伸出长臂环住他,路修远还会愿意给他一个吻,安抚他的闹情绪,依着他待在厨房里做一个小尾巴。
漆黑夜色里,月光驾车而行,慷慨地将自己的光辉洒遍每一处,宠幸着属于、或不属于它的信徒。
晏冷淡慢慢走到一楼的淋浴间门前,他知道里面有一扇磨砂的玻璃门,会随着水声渐涨而水汽环绕。有时他们累了,不愿意上二楼,就会在这里清洗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