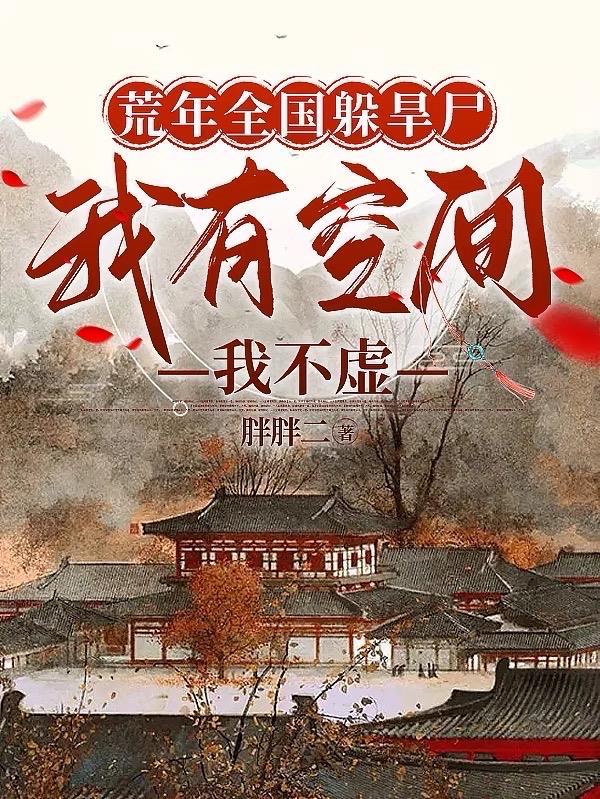极品中文>女匪首大结局 > 39 第 39 章(第2页)
39 第 39 章(第2页)
那游医也不是个好的,想着林家有钱,定肯花大价钱了事,正巧自己家中就有剩药渣,二人便挑挑拣拣,生拼了一副药渣出来,商定赔偿金五五分,这才一唱一和地找上医馆。”说到最后,阿虹唏嘘不已,“方老千怎么打怎么罚都不为过,就是可怜他的老母亲,为儿子操心大半辈子,最后还无法安葬,尸只能暂停于义庄。”
寒风料峭,林越舟忆起那老妇人面容,眸色一闪,心中泛起阵悲凉,从腰间蓝色小荷包中掏出银子来递给阿虹,“买个棺材帮那老妇人下葬了吧。”
阿虹拿着钱有些怔然,“越舟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从前没有钱都要搞些钱出来,现在荷包里有几个闲钱,既遇上了,便当是积德。”
她气定神闲地站起,招呼着阿虹起来继续练武。
苍天寒地,宅里另一角的软屉箭腿榻上置着矮几,矮几上烧着个炭火小炉,隔着一寸见方的铁丝网格子,上烫着壶热酒并几个大红枣子,酒已温热,时安却没有动它的意思,直到石大裹挟着股寒风进来,他才给两个银酒杯斟满。
石大将褡裢随手丢在榻上,哈着白气道:“公子,江南茶盐司公署就在江州,我买通了个书吏,那人说良这几日都没来茶盐司,好像有啥急事出城去了。”
一句话讲完才拿起热酒吞下,去了大半寒气。
“可知何时回来?”
“书吏哪知道这些,不过他说十月十五下元日前必是会回来的。”
他轻抬眼睑,眼里透露着一丝疑惑,“为何?”
“公子有所不知,这江南地界行商多靠水路,而下元节正是水官解厄的日子,比之西州,这节在江州办得可热闹了,城里上至州官巡使,下至贩夫走卒,都等着这天延道设醮、消灾祈福,祈祷来年银票多多呢。”
“良升任江南茶盐使也就这一年的事,他掌茶盐之利,以充国库,少不了和商会打交道,听说今年便是由他主办下元节冬赏会,届时各家商户的游船画舫都集中在柳河至陵江段,而良会在其中最大的一艘楼船上招待江州商界有名的老板。”
时安捏起一个表皮微焦的枣子递过去,沉吟道:“这么说,林家也在受邀之列?”
石大眉毛一翘,吐出滚尖的枣核,略兴奋道:“不仅如此,公子猜猜那艘楼船是哪家营造局承办的?”
时安淡淡一眼扫过去,双唇轻抿,颇为无奈,“想必就是林家吧。”
“可不是嘛!”
石大激动地一拍桌,“我们能事先藏那船里头!”
炭火熏烤得屋内闷热,时安不作答,走至窗边支开一丝缝隙,朔风吹起额前碎,泛红的鼻尖轻吸了口冷气,目光清明,转头看向饮酒自乐的石大,肃道:“这法子不行,林家营造局的楼船出了刺客,你让林家如何跟上官交代,以后又如何在商界自处?”
石大半张着口,眼神闪躲,嘴里的酒都变得无味起来,一拍头道:“都怪我喝酒喝上头了,这医馆的事才过去,不能因我们让林家又出乱子!
公子,我自罚三杯!”
“我看你就是馋这口酒。”
他摇摇头不做计较,负手问道,“另一件事呢?”
石大拍着胸脯保证,“我办事公子还不放心嘛,棺材已经置办下了,明天就去义庄帮老妇下葬。”
“如此,便好。”
时安将手悬至泥炉上,红光照映,薄皮下的青筋隐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