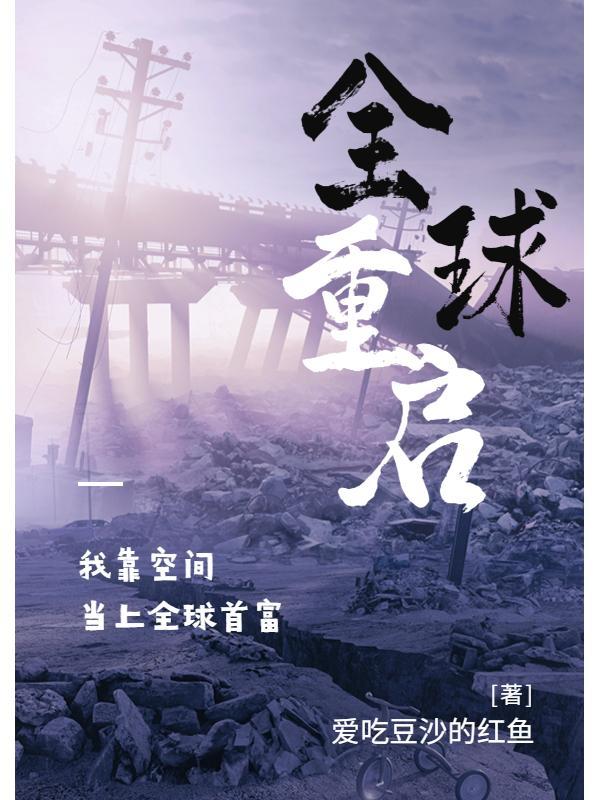极品中文>欢迎回家的诗句 > 第41节(第2页)
第41节(第2页)
幽暗中看见彼此的眼睛,丛欣也终于对他说出来:“我是真的想过去找你的。”
“什么时候?”时为问。
他当时一直惦记着那句话,他上飞机那天,她发给他的消息,再见,为为,如果有机会,我会去看你的。但她一直没有来。
丛欣却没有直接回答,从头说起来:“我上了大学就一直在打工。”
时为问:“都干过什么?”
丛欣说:“比如在肯德基带着小朋友跳舞。”
时为笑了,评价:“终于活成了小时候向往的样子。”
丛欣也跟着笑起来,又说到后来:“还有大二暑假,在嘉年华上卖爆米花可乐赚了一笔钱,发财了。”
时为又问:“赚了多少?”
丛欣说:“两万多。”
时为夸她:“不愧是领导。”
丛欣无所谓他的揶揄,只是接着说下去:“那之后就开始做攻略,打算大三暑假去看你的,办签证要用的学校证明都开好了。”
时为问:“后来为什么没来?”
他记得自己那时候有多想念她,甚至做过这样的梦,他在宿舍里,听到门外她叫他的声音。
记得那时每次都是把她的名字搜出来,看着空对话框,打字,删掉,再打字,再删掉,最后什么都没发出去。
丛欣静了静,才回答这个问题:“我跟你说过的,我妈妈在澳门做了两年,那时候刚去新加坡,在金沙工作……”
她看着月亮,继续往下说:“那是个两千五百多间房的超级大酒店,别人提起来,想到的大概都是赌场,无边泳池。但我总会想到背后那些服务员,感觉就跟蚁穴里的工蚁似的。每天上千间客房的大进大退,厨房一次做几千人份的早餐。
“我知道她在那里工作肯定很辛苦,但她从没跟我说过到底怎么样。只有一次,我跟她打电话的时候,听她声音有点不对劲。我以为她感冒了,就盯着她问,但她突然哭了,后来还是因为怕我担心,才把事情告诉我。她那天做房的时候遇到一个客人,因为对方是华人面孔,接手机也用的是汉语,她就没跟他说英文,结果就被投诉了。主管带她去跟人家道歉,被那人阴了几句,叫她滚回自己国家去。”
她说到这里轻轻笑了笑,像是自嘲,也像是事情过去许久之后的释然:“其实就是这么一件小事,我那时候跟她两个人打着电话哭了半天。我说妈妈别干了,回家来吧。但她哭完就好了,说我干嘛不干啊,他让我回家去我就回家?一年二十万呢!我俩又在电话两头一起笑出来。但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我没办法那么挥霍,花两万块钱去旅游。”
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这么现实的理由,但他字字句句都明白。他不也没回来吗?
朱岩最初在瑞士的那几年收入很低,当地生活开销又很大,一个人在异乡重新开始不是那么容易的,还要供他这么个大孩子读学费不菲的私立大学和烹饪学校。
而且就算见面了又怎样呢?他们那时候幼稚渺小得不值一提,也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注定还要分开很久很久。
两人不约而同地沉默,直到时为又开口说:“后来你给我发过一条拜年的短信。”
丛欣看他,惊异他竟然还记得,但惊异之后便发现其实自己也记得。
“你没回。”她说。
“一看就是复制黏贴群发的,”时为控诉,很嫌弃地说,“就那种新春大吉,心想事成,一切顺利。”
“但是你没回!”丛欣也控诉。
时为没话了。
是的,他没回。收到那条信息的时候,他当真觉得自己失去了这段自出生开始的友谊,他变成了她联系人列表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哪怕两人一句话不说的那几年,他都不曾这样想过。
于是两边都伤了心。
丛欣说:“后来那年,我没发给你,你总该知道不对了吧?”
时为说:“我以为你把我拉黑了。”
丛欣说:“你不试试?”
时为说:“我不敢。”
丛欣又笑了,有些无可奈何,当时一定是难过的,但时过境迁,一切仿佛都变成了一个有趣的误会。
时为看着她,说:“我那时候已经到了巴黎,在我说过的那家凯旋门附近的中餐馆里打工,就是春节时候,在后厨的墙上看见四个小小的圆珠笔写的字……”
“什么字?”丛欣问。
时为说:“我想回家。”
丛欣心里轻轻地震动,却还是狡黠地笑看着他问:“你那时候哭了吧?”
时为避开她的目光,点点头。
牛羊反刍一般,他们回忆过去,那浅浅的一杯酒也喝完了。
丛欣放下酒杯,看了眼时间,起身说:“我走了。”
她其实并不想走。
他竟也看出来了,跟着站起来,再一次拉住她的手,把她带入怀中。
却是丛欣先吻了他,仍旧是浅浅的触碰,而后无声笑了,很近很近地看着他说:“你不会又要逃走吧?”
时为说:“这是我住的地方。”
丛欣问:“那你会不会赶我走?”
他摇摇头,把她整个抱起来。
她再次感觉到一阵身体深处的潮涌,手捧住他的脸更深地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