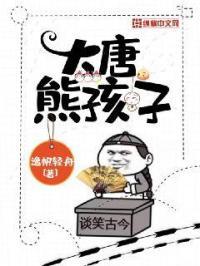极品中文>杳杳如年TXT > 第43章(第2页)
第43章(第2页)
桑岱一屁股坐到床上,顿时感觉困倦涌上头顶。他打了个哈欠,将佩剑抱在怀里,倒头躺下便睡。
这张床非常非常舒服,桑岱觉得自己从出生到现在,从来都没有躺过这么有安神功效的床。
他久违地做了个冗长的梦,梦里不留行破破烂烂的山门前站着许多人,指着挑水回来的他哈哈大笑,连他师父那个老头子也站在门口,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笑什么!”他气急败坏,“告诉你们,小爷可是会飞的!那些灵修都跟我称兄道弟,小爷以后再也不挑水扫地了!”
然而那些人离他越来越远,他追过去想要进门,院门却在他眼前砰的一声关上,任是怎么拍打也纹丝不动。
梦醒之前,他迷迷糊糊听到了门开的声音。
桑岱嘟哝着翻了个身,挠挠脸,觉得越睡越热,仿佛有一道视线落在身上,如同麦芒一样刺着他。
他打了个激灵,慢慢睁开眼,看到一个绿袍少年坐在床边,正面色阴沉地看着自己。
桑岱一下子坐起来,先去找自己的剑,硬撑出几分聊胜于无的气场,支支吾吾问道:“你、你是谁啊?”
绿袍少年也起了身,个头比他高出去些许,居高临下地望着他,眉眼间极有压迫感:“我还想问你——你是谁?”
“这屋子是你的?”桑岱心虚不已,还是抱着一丝侥幸问道。
绿袍少年不语,神情还是冷的,只是往前走了一步,几乎将他堵在了床角,退无可退。
桑岱只觉得头皮一阵阵麻,眼神乱飞,慌乱道:“难道晏伽没骗我?这屋子真有人住啊……”
绿袍少年闻言,瞳孔猛地缩紧,伸手扯住他衣领,急促道:“谁?你说谁?!”
桑岱被吓了一跳,在别人的地盘上也不敢惹事,只得窝囊地推了推对方的手,讪讪笑道:“你、你不认识晏伽啊?他还吹牛说什么自个儿在越陵山面子可大了,满地都是熟人,怎么谁谁都不认识他啊……”
绿袍少年看他这废柴脓包的样子,冷笑了一声,将人放开,恢复了先前那种有些高傲的姿态:“他现在就在越陵山?”
“对啊!”桑岱急忙祸水东引,“不信你去问问,他说这里他说了算数!”
“好。”少年笑了笑,“你跟我一起去。”
草庐里点了沉香,床帐外氤氲叆叇,帐子里人影动了动,低声私语着。
顾年遐身上披着衣服,半掩着青红遍布的肩头,手指绞了晏伽的头在摆弄,耳朵抖来抖去,故意在引人注意。
“动什么?”晏伽按住小狼耳朵,“安生点。”
不过确实很软,晏伽忍不住又摸起来。
顾年遐喜欢被他摸耳廓,白色绒毛包裹着那里细嫩的肌肤,很是敏感,晏伽有些粗糙的指腹划过去的时候,总能带起阵阵颤动。
“小狼毛弄脏了。”晏伽低头对着他笑出声,“出来洗洗。”
顾年遐起身抱住他,衣裳从肩上滑落,又被晏伽提起来:“以后好好穿衣裳,别哪天又喝醉了,我怕你光着身子到处跑。”
两人收拾干净,准备去做些正事,就听到外面放鞭炮一样闹起来,晏伽听出好像是结界之外的响动,离这里不远,似是有大事生。
顾年遐最近脾气越大,皱了皱眉,起身穿衣服:“有完没完,又是谁来踢馆了?带我去看看。”
晏伽站着没动,盯着他看。
“怎么了?”顾年遐疑惑,
“刚才凶得吓我一跳。”晏伽道,“本事不小啊现在。”
顾年遐扑上去啃了他嘴唇两口,身体力行地凶给他看。
此时越陵山东南结界之外,凌绡正领着数十弟子和一干凌绝宗人对峙着,她踏在剑上,右手已经捏满了一道咒诀,若对方忽然难,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将此杀招出手。
凌绝宗自然也知道越陵山里都是些什么人,轻易不敢上前,只是仗着人多,也有了几分胆量。
“我只说一遍。”凌绡冷然道,“滚出去,你们还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