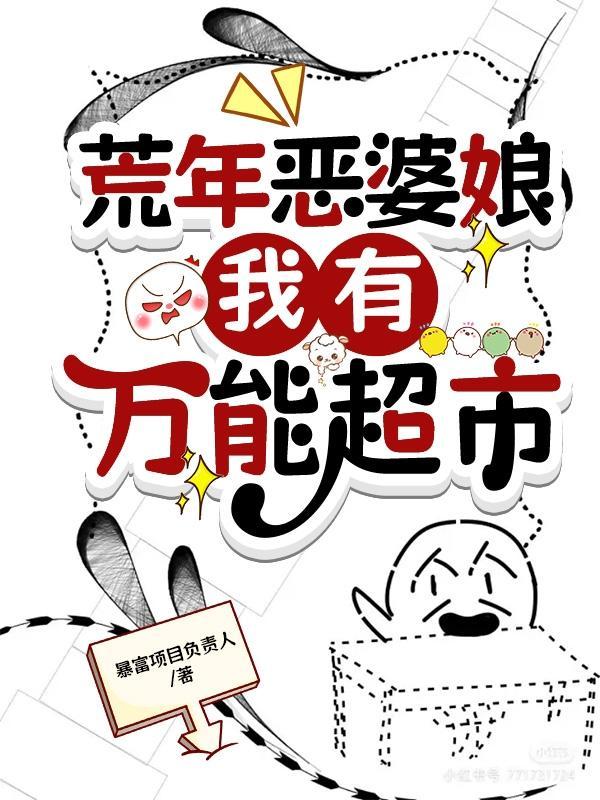极品中文>那些得不到保护的人好看吗 > 第53章(第1页)
第53章(第1页)
“三名‘犯人’的犯案现场,这是你们家的孩子,没错吧?我看我们凭这个就可以跟你们要赔偿了吧?”
这群父母的脸色由红转青,逃跑似的离开了。
“不过,怎么偏偏都是些没担当的笨父母啊。这是为自己的孩子撑腰呢,好歹该多坚持一下。”
第二天,听闻这件事的惠在利根和官官面前哈哈大笑。
“不是啦,惠婆婆,就算是儿子,证据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就哼也不敢哼一声了。现在学校对霸凌又管得很严。”
“其实不是管得很严,是很怕霸凌的事实暴露出来。”
当事人官官此时也一脸神清气爽地参与对话。
“小学的时候也是这样。班主任每个月都要
问一下‘我们班上没有霸凌吧?’然后全班同学回答‘没有——’,就结束了。明明就不可能没有,可是像例行公事似的问了,老师才会放心。”
听官官这么说,惠不禁伸出舌头。
“老师这个职业也快堕落了。官官上的中学都这样了,要是我们没管,还得了?”
“就算他们恼羞成怒,我们手上也有照片当证据。他们不敢再对我出手的。”
官官得意地秀出数码相机。
那时候,拍下三人涂鸦现场的就是官官。他从捕捉到犯案瞬间的三天前就一直和利根一起监视,想必加倍欢喜。
但这次提案的是惠。既然被喷了漆不甘心,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惠这样教他们两人。
“泼他们一头油漆算是处罚得恰到好处。再严厉一点,就从被害人变成加害人了。所以呀,官官,你要趁现在和那三人和解,这种事越早越好。”
官官显得很意外,问道:
“都闹成这样了,还要跟他们和好?”
“制造敌人不如结交盟友。人就是要盟友多才强大,而没有多少人敢与强大的人为敌。你觉得哪一边比较轻松?”
3
对利根和官官而言,惠扮演了父亲的角色,同时也是母亲,但正如同有些事不敢对亲生母亲说,有些事他们也不敢找惠商量。这对利根来说,就是工作方面的事。
利根当时在“登坂铁工所”工作。社长登坂是个富有爱心的人,利根与小混混发生暴力冲突,他不仅没辞退利根,在法院开庭时还赶来旁听。
“我有前科,为什么您还肯让我留下来?”
利根这么问的时候,登坂以有些为难的神情这样回答:
“因为利根你在铁工所里又认真又绅士,没麻烦到任何人,打架也是在下班时间发生的,我没有理由要你走啊。”
他住的是搭建在铁工所旁的宿舍,房租非常低廉。薪水虽然不多,但利根对老板的为人印象极佳,所以很喜欢这里。
只是,有爱心的人不见得都善于经营。不,也许会热心助人的人都不适合当老板。登坂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气氛就能感觉出“登坂铁工所”的周转一天比一天吃紧。车床机老旧了,他也迟迟不引进新机具。稼动率降低,登坂也不以为意,这便意味着订单本身减少了。
尽管从气氛中隐约感觉到经营越来越困难,但利根进公司日子还短,也帮不上忙。才抱着毫无根据的希望,相信登坂一定会渡过难关,头一个灾难便降临铁工所——第一次跳票。
连社会经验不多的利根好歹也知道跳票意味着什么,就是
付款资金不足,无法支付应付的面额给债权人。就算第一次设法筹出来了,要是六个月之内又发生第二次跳票,银行就会停止交易,无法获得银行融资。换句话说,便是事实上的破产。
登坂不顾大多数员工的担心,第一次跳票虽延迟仍付清了。但他的付款方式正是踏入无间地狱的第一步。
“有人看到我们的窘境于心不忍,伸出了援手。”
登坂笑容满面地向员工报告。他为筹钱不断奔走,但银行和客户都见死不救,直到最后一刻,他遇见了“救世主”。
“他把银行也不愿意借的大笔资金低利融资给我们。实在太感谢了。”
登坂恨不得跪拜似的介绍了一个姓神乐的男子。神乐年约六十,温和的笑容令人印象深刻,他以菩萨般的眼神环视在场的工作人员。
然而,神乐不仅不是菩萨,根本就是夜叉。融资的第二天,神乐便出任“登坂铁工所”的常务董事。他是提供资金的金主,这件事本身并无不自然之处,问题在于登坂没有看人的眼光。
不到一周,神乐便过度干预经营,他以“经营太随便”“营销能力不足”“先行投资方向错误”为由,从外部找来“足以信赖的人才”。这些男人个个神貌可疑,相比安排他们在办公桌前敲电脑,在赌场打赤膊杀红眼还更合适。于是铁工所的经营权便眼睁睁地落入神乐那一派的人手中。不久登坂
与员工便得知神乐是地方暴力团组织的事实。
这是典型的掠夺。
登坂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老板,只
会对神乐唯命是从。登坂的命令其实就是神乐的命令,员工也只能按照神乐的意思行动。
“掠夺”与“侵吞”是同义词。要不了多久,他们便强制原本的员工加入暴力团。
“只是登记个名字而已,不会要你们去做危险的工作的。就像幽灵社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