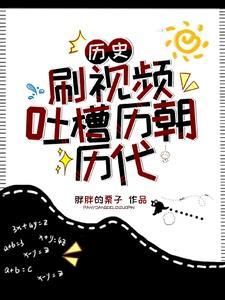极品中文>杀死那个作家 > 第255章 小嘴这么会讲话快给我亲一口(第1页)
第255章 小嘴这么会讲话快给我亲一口(第1页)
班莫对于阿哥这个人,其实很难说准。
族人们说那是擎起第一簇火种的人,是祖先,是山神,是沉寂的石像经年累月守护的家园。其提哈每一次振动双翅,生出来的风就带走了那片灵魂。
群山环绕自然而成的祭坛原来叫做谷底,班莫住在这儿,他看不到雪山之外,但他的头顶有永恒之光,被带走的灵魂会成为不朽的星星,那是北姑对他和族人最好的馈赠。
而群山也在俯视谷底,一低头,便能看见族人的生死,瞬息就度过了他们的千年。
北姑不是突然变成冰原的,但它一望无垠,或有可能以前曾是草场。班莫把鹿哨递到唇边,悠远的余音让万物化生,好像还有祖先与神灵常在的痕迹,指引失路之人慢慢回到故乡,继续种下他们未完的星火。
他的阿敏麦是上一任族长,有关阿哥的故事历久弥新,是一代人又传给了下一代,矢志不渝地护着他们的根。族人对家乡的眷念已经深深刻在骨肉中,支撑他们的正是那些昼出夜归的艰苦岁月,只要记忆永不灭,阿哥就能永远存在。
后来班莫逐渐明白,他们只是把对雪山的敬畏,都凝聚到了一个人身上而已。
以血肉之躯比肩神明,本身就是奇迹。
所以阿哥,其实可以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儿时班莫就常对玩伴说,他会成为阿哥,会带领族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最后换来的是他走不出大鹿谷,是一句与好友的“难得一见”。
他们和石像一样,都被困在了原地。
眼前有模糊的身影,班莫的鹿哨越来越响了,他站在天与地的祭坛上,仰视山巅召唤了一段古老的记忆。而在梦里,歌钟非旧俗,神鸦社鼓带来多年的符瑞灾异,山墙下鬼神的塑像也依旧庄重,细数生死殊荣从指缝流泻,岁月失语,惟石能言。
繁华落幕,新阳又会升起,即便他们都不存在,山塑仍然伫立着。
当角鹿结群归家,族人陆续运回他们的猎物,班莫却记起来了,在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人也曾从这里出。
班莫凝望那抹身影渐渐清晰,谓红炉点雪,她可探手斗垂天,翻起波浪万顷,又似流波化盾,一次勇,二次燃,再听愈惊,连山呼都不得她孤标风雅。
明若清不循苟且,她的力量皆从北姑而来,因此取受用之不竭,昔日枷锁便如流云。翱翔的鹰不会被高山所困,若生不逢时就拔刀痛斩,她挥出凛冽寒芒,无剑却有风雷之音,全凭自身登上了无人之巅。
适逢鹿哨声转急,她踏步翻身,一指划破孤冷,一棍打出变色,须臾间枯叶纷崩,其后松盖顷然倒下,激起碎琼漫天斗转,再一次浸染了她的身躯。
世事有万般变化,譬如花落花开,重之又重,因此逆溯的不止是山中雪。
前人在这里遥望着故乡,事了拂衣去,没有留下半分名字,但唤一声延寿客,他就回了头。
从少年意气再到步履蹒跚,不知是谁蹉跎了谁,唯独记得他离开时,有身后北姑替他作答——
老先生去也。
“冰雪之在人,如鱼之于水,龙之于石,日夜沐浴其中,特鱼与龙不之觉耳。”
是明若清在说,还是这座雪山竟深藏了他的声音好多年,借她之口完成了一段遥远的对话,到最后班莫都分不清了。
靠着无形无相一念开明,依班莫所见,哪怕她要登仙也是天然。
就和当初在抱子坞找人一样,上山来寻明若清的各位其实也旁观了许久,是以她的变化都看在眼里,不过短短一个月,能修成这样确实值得敬佩。
南初七道:“哟,棍仙呀。”
姜云清道:“有浮云、白雀之徒,借其力而登天。”
因二人几乎同时开口,说完后又双双沉默了。
南初七觉得不对,姜云清觉得不该。
唐沂站在他们中间,率先打破僵局,主观评价道:“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区别。”
姜云清本想替南初七找补几句来着,谁料他窸窸窣窣凑过来,腆着脸道:“小嘴这么会讲话快给我亲一口!”
姜云清没怎么思考,只是单纯地不习惯在外人面前亲密,有昔日被老庙祝撞破的经历在,下意识用一巴掌回绝了南初七的要求。
效果极好,南初七不耍流氓了,但反手给了唐沂一拳。
唐沂摸着胸口:“?”
他都不想说,希望这俩狠狠锁死。
待人走后,姜云清才反应过来说声抱歉,问南初七疼不疼。
南初七抵着脸颊内侧,作势回味了一下,疼肯定是疼的,不过——
“其实方才生风过来最先闻到的是哥哥手上的香,等到巴掌落在脸上反而就不那么痛了。”